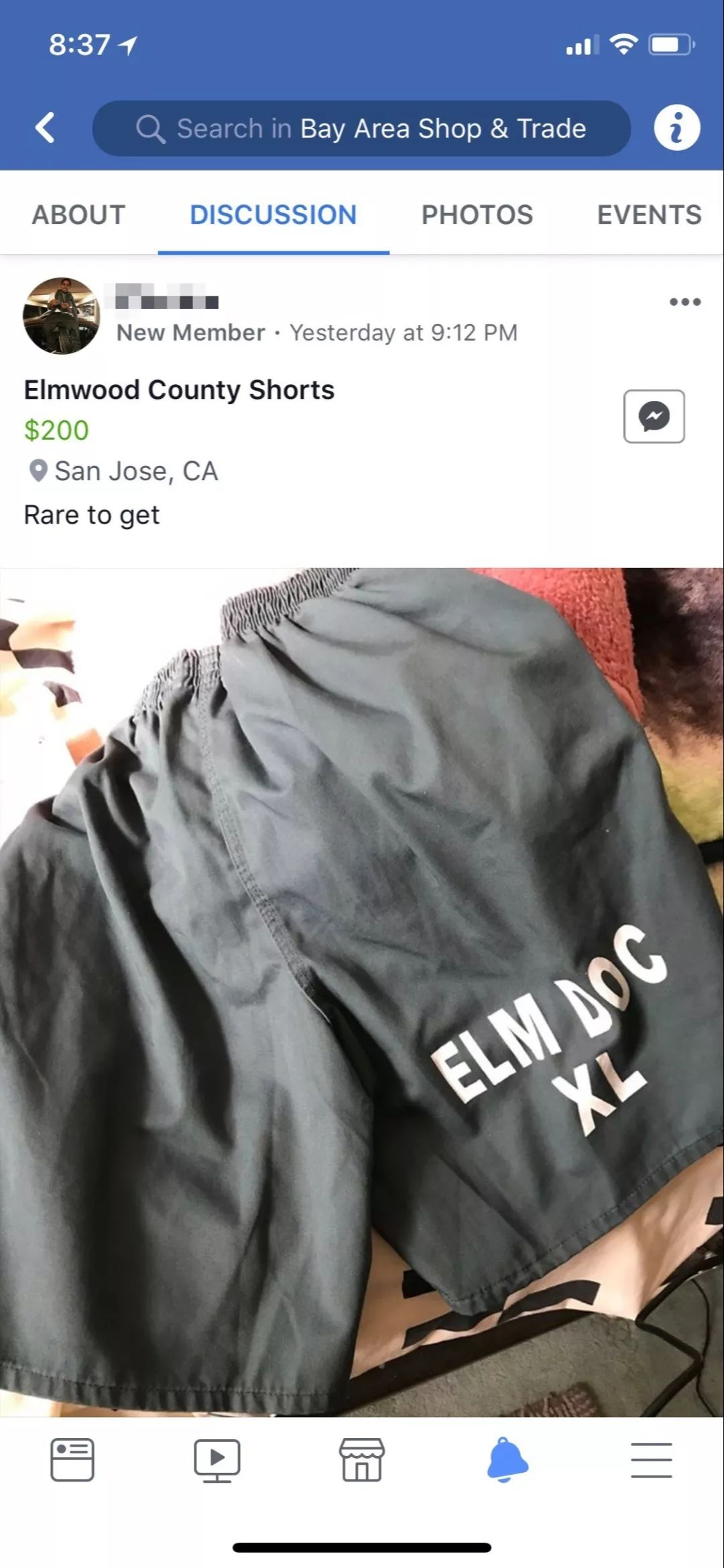2025年的正月,在運城市萬榮縣大禮堂裡,一連上演了六天的笑話晚會。沒有海報,沒有門票,人們互相通知著來到現場,場場滿座,笑聲、掌聲自發地響起來。
這是個能談笑風生的地方。35年前,就在晉南的這個縣城,一場收集笑話的行動開始了。
行動由一些文人展開。《山西日報》記者管喻剛到運城記者站工作,東奔西走,常聽到笑話。他熱愛民間文化。飯局上,他把笑話關鍵詞記在手心上、衣服的邊角上——偷偷地寫,以免破壞氣氛。20個徵集笑話的銅牌掛在運城各縣小飯店裡,萬榮縣最多,誰講一個笑話,可以免費吃一碗羊肉泡,管喻來結賬。管喻還在報紙上登廣告,公佈徵集笑話的電話與地址。電話裡,有時,對面的人講出一個笑話,還沒等他問一句,一下掛掉了——電話費那時很貴。
2008年,這些流傳在民間、“風一樣刮過來刮過去”的笑話,最終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笑城
進入山西省萬榮縣城,縣界“大門”楹聯上掛著“笑城”一詞。
在縣城的笑話廣場上,警務亭打出的電子標語裡除了健康、共享,還有:激情、快樂。一位居民說,這些年,縣城裡笑話元素“不知不覺”變少了,但一些公共廁所裡、車站裡,都還貼著笑話。
這裡有笑話比賽、笑話晚會、笑話點播臺、笑林印刷廠。笑話村食府是萬榮笑話的起源地謝村附近最大的飯店,飯店的選單上、牆上都曾經印了笑話。20世紀80年代後,電影放映員郭澄沒什麼活幹了,開始主持鄉村的紅白喜事,笑話起初作為串場,後來成為正式的節目上演。如今他是全縣聞名的笑話明星,出門常被認出來。
當萬榮人開始講笑話,總是要拉開架勢。幾個經典動作是:身體前傾,右手背使勁兒拍在左手心,跺腳。
“這就是真事兒!”萬榮人在講笑話時常說。管喻模仿起那種激動的神態:“這就是我村的事兒!”“這就是我行(巷)裡頭的。”如果聽的人再不信,或許會說:“實話和你說了吧,這其實就是我屋(家)的事!裡面的老太太就是我媽!”
強調真實,是一種自發的表演策略。“一下子把他抓住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麼,你不感興趣啊?”萬榮縣城鎮中學語文老師、萬榮笑話的傳承人之一王新棟說。萬榮笑話是“無主的”,在生活中“摔打”,大部分不存在創作版權,每個人都可以“添油加醋”。它適合講而不是讀,文字、普通話都會使效果折損。
萬榮笑話被認為最早起源於明末清初。笑話的主角曾是掌櫃的、地主、長工、秀才、莊稼漢、公社幹部。後來變成山裡人、農村人、城裡人、廠長、局長、縣長。起初,笑話來源於主人公沒見過鏡子,沒坐過轎子,沒看過戲,不會算賬,不識字……後來,笑話又產生於買電扇、用電燈、坐公共汽車、坐火車、看病等生活中。
現代化程序中的時空錯位造就大批笑話。
以前,“山裡人”不知道怎麼郵包裹,小偷說是把包裹綁在電線上。主人公照做,被小偷拿走了,他還暗自高興“這郵得就是快”!有人第一次見到手電筒,特意等天黑了,照著明回家,卻發現不知道怎麼關掉,吹不滅,拍不滅,最後想到了好辦法:把它埋進糧食囤裡!
再過一些年,電燈的笑話就太老了。故事裡的人們賺到了一些錢——來到城裡,農民老牛看到熱門掛曆卻沒買,因為看上面的女孩穿得少,“比咱村那幾年還窮哩!我不想看見人受窮!”一名煤老闆的兒子去北京上大學,告訴爸爸,這裡同學都對他很友善,只是別人都是坐地鐵上學,只有他坐奧迪。那名煤老闆趕緊給兒子打去50萬元:趕快買個地鐵坐坐,“別給我丟人了”。
一些高雅的也被解構了。一名文人來到村裡,農民把作協的聽成做鞋的,把出版社的聽成做木板的,並告訴他們,不需要鞋,但需要打個木板。一人到麵館吃飯,說“來碗新局面”,疑惑“沒有這個菜你們寫在牆上幹啥”?
大約1999年的一天,時任萬榮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的李廷玉第一次見到管喻。那時管喻已經出了一本《萬榮新笑話》,出版社說想要更多。李廷玉幫忙徵集笑話,兩個多月,宣傳部就收到約600封信件。
“進入笑話王國,謹防笑掉大牙”
那是萬榮笑話發展巔峰時期的開始。進入新世紀,40多歲的衛孺牛來到萬榮縣擔任縣委書記,提出打造“笑話王國”的構想。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自己生長在與萬榮縣接壤的臨猗縣,從小就聽過萬榮笑話,也知道這裡乾旱、貧窮,沒什麼礦產資源,工業與農業發展都受限。“宣傳定位,應該是以文化往外打”“帶動產業發展”。他自稱,剛到萬榮縣他性格內斂,一個笑話也不會講。
但後來在萬榮很多人記憶中,他是萬榮最會講笑話的人之一。當時在縣委宣傳部工作的80後韓維元記得,萬榮縣電視臺轉播或錄製的萬榮縣兩會成為熱門節目,很多人從熱播電視劇換臺來看,要聽“衛書記說了啥”。韓維元還記得,有時開著會,衛孺牛講著稿子,突然坐不住了,眼鏡一摘,講自己的話,現場鴉雀無聲。
“笑話是世界上最珍貴的資源。”“你難出一個笑話段子讓人笑。”“笑太好了。”衛孺牛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咱們過去把笑話看低了”。

1999年,萬榮縣首屆講笑話大賽上,電影放映員郭澄正在表演。受訪者供圖
一個“笑話王國”建立起來了。有“笑話機關”“笑話企業”,財政局走廊貼滿了笑話,放著“哈哈鏡”。幾家文化公司研發了笑話掛曆、笑話撲克、笑話雨傘,象徵萬榮逆向思維的倒轉手錶,錶針倒著走。這成為萬榮紅極一時的外出送禮產品。李廷玉回憶,當時縣委書記在全縣幹部大會上,要求所有幹部會講笑話,出去招商引資,能開啟局面。有人找李廷玉來要笑話書回去學習。
手裡一張名片,背面朝上遞過去,名片背面印著笑話,衛孺牛回憶起這樣的動作。當時,萬榮很多公務員都有這樣的笑話名片。這樣的名片遞上去,李廷玉說,“肯定就不一樣了”。他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笑話的流行給當時萬榮人出門辦事提供了極大便利,要不然,“你有什麼特點啊?”
2003年,時任萬榮縣縣長的武宏文在深圳辦了一場“賣笑話”招商引資會,現場賣出了上千套笑話圖書和光碟,還簽了近兩億的投資意向書。大約2006年,鄉鎮醫生黃泰把一本當地的笑話書放在枕頭底下,每天睡前看幾個。因為醫院裡來了幾位外地專家,每天都纏著讓他講笑話。這樣的場面在很多普通人身上發生,韓維元日常準備了兩個笑話,應對不同場合。
萬榮縣一位退休幹部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2006年前後,他去上級單位申請經費,到了辦公室,他給在場人講笑話,距離拉近了,“話也才慢慢地說開了”。
2008年,笑話博覽園落成,以一個哈哈大笑的臉作為門的造型,姜昆、敬一丹曾經到訪。在笑話博覽園,有一面萬榮笑話牆,印著約一萬個笑臉。衛孺牛說,其中很多是他讓攝影師從民間收集來的。衛孺牛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他當時還有夢想,辦一份全國發行的笑話報刊。當時,進入萬榮縣城的第一個門樓上,掛著這樣的楹聯:“進入笑話王國,謹防笑掉大牙”。這是李廷玉寫的,他記得有人覺得這句話俗,但衛孺牛選了這個。
李廷玉覺得那是一段充滿激情的歲月。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們)就是這種觀點。”
為了讓萬榮笑話登上當時的央視熱門節目《曲苑雜壇》,李廷玉和其他官員一起來到北京,尋找素不相識的製片人。萬榮縣特產蘋果,當時蘋果與笑話聯姻,蘋果箱裡也放著笑話卡片。在蘋果成熟前兩個月,表面還未被曬紅的時候,他們在蘋果上貼字,蘋果成熟後,能映出:“你好”等字。來到央視,他們扛著兩箱蘋果上樓,見了面,就對節目組的人講,這些蘋果是怎麼來的。
“乾旱,貧窮,人還能行。”這是當地很多人記憶中衛孺牛的話。關於乾旱,衛孺牛會用這樣一個笑話講出來。萬榮的大黃牛出名,但萬榮太乾,乾草多,牛吃不到鮮草,有人說,給牛戴墨鏡,乾草就變綠了。貧窮藏在這樣的笑話裡。包產到戶之前,萬榮一戶農民年年吃不飽飯,每年祭灶時都會貼上這樣的春聯:“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但農民覺得,年年讓灶王爺說好事,還是年年吃不飽,索性在某一年貼上這樣的對聯:“上天去說啥算啥,回來後想咋就咋。”

電影放映員郭澄手機裡記錄的笑話創作靈感。郭玉潔/攝
“光(是)這對聯的笑話,我能給你講幾十個。”衛孺牛說。
2010年,《記者觀察》上刊載一篇作家採風遊記。作家王西蘭記錄了與當時的縣委書記衛孺牛的交流。有作家疑惑:萬榮笑話,怎麼全是自我嘲諷?自我揶揄?
衛孺牛當時說,萬榮笑話的特點之一是“自己笑話自己”,骨子裡頭,萬榮人是自卑。“你想,祖祖輩輩連水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喝,連臉都不能幹乾淨淨地洗,還能不自卑?還能不苦澀?還能不承認自己的卑微?”
“改革開放了,別的地方都在日新月異地改變著面貌,萬榮怎麼辦?不改變行嗎?”“萬榮人沒有後路只有背水一戰,萬榮人對改革開放最理解最擁護,萬榮人改變落後面貌的心情最迫切。”當時他說。
在萬榮有句俗語,“除了死法都是活法”。衛孺牛覺得,正是在過去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很多萬榮人形成了偏執、逆向、不按常理出牌的思維。他在萬榮工作期間感覺到,很多萬榮人“想得大”。
縣裡一個小規模果庫,起名華北果庫。一家當地滑雪場,起名國際滑雪場。一個小單位領導來找他,說希望當教育局局長,他說,教育局局長已經任命了,你不知道嗎?對方說,他管西半縣,我管東半縣,看我倆誰管得好。還有一位農民,給水利部部長寫信,謀劃出北方抗旱建議:從喜馬拉雅修一條大渠到內蒙古,透過水分蒸發,增加大氣水分含量。
李廷玉記得,那些年,外地人不是覺得他們會講笑話,而是覺得“你們這些人就很好笑。因為你們這些人說話做事都不一樣。因為笑話和你們融為一體了”。
鄉土社會
李廷玉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那一時期笑話大量湧現與這種背景有關:大量農村人進城打拼,農業社會思維和市場經濟思維劇烈碰撞。
當時,這樣的形象出現在笑話中。孫爭在北京打餅子賣切糕做蛋糕,掙下幾個錢,穿著一身名牌衣服,戴著彩色眼鏡,腰裡掛個BP機,撇著洋腔回來了。見了人沒別的話,一口一個北京好,北京什麼都好。北京的茅房是香的——灑香水呀!北京發糕是甜的——起碼攪一半白糖。村裡人都說他:燒包!
萬榮笑話的主角是農民,笑話裡的城市,也大多是透過鄉村的視角打量。
最早,萬榮笑話發源在一棵鄉村的柳槐樹下。
柳槐樹在萬榮縣榮河鎮謝村,這是一個曾有9000多人的大自然村,處在交通要道上。柳槐樹正處在人流匯聚的中心,拉煤的,販鹽的,彈棉花的,小商販南來北往。在柳槐樹下,“諞(方言,指閒聊)”笑話是日常,“諞著諞著這謝村掙(方言,此處指一些充滿傻氣的笑話)就出來了。”如今村中幾個70多歲的老人在一起回憶。
時間長了,這個交通要道上的村子以笑話聞名。那些真假參半的傻人傻事,都被安在謝村人頭上,成為恥辱,甚至引發過青少年間的群架。

2月24日,75歲的薛兩省在謝村,他是謝村最會講笑話的幾個人之一。郭玉潔/攝
半個世紀中,人們對笑話的態度幾經變化。20世紀80年代,有文人來到村中採訪,收集笑話,曾被人罵出去。薛兩省曾任謝村村支書,他記得有人把謝村笑話收集起來,登在報紙上,他們很生氣,要求報紙公開道歉,恢復名譽。新世紀,政府開始開發笑話,講笑話“慢慢地”變成好事。萬榮縣建設笑話博覽園時,因為選址不在謝村,而在景區,謝村人也曾提出意見。
漫長的時間沖刷了笑話中或褒或貶的色彩,如今講笑話本身成為一種景觀。村中偶爾有外地的學者、學生來訪,瞭解笑話的事。每次來人調查笑話,老人就把這些笑話講一遍。
“胡諞,熱鬧一個。”從薛兩省充滿激情的表演中,能看出他並不覺得乏味。他模仿著他幼年時村中一位“老漢”講笑話。連帶著那些笑話表演中的語氣、停頓、轉折也被努力復原。這位老漢可以從來訪者一句話,一塊手錶,現場編出一個笑話,講著講著“就把你罵了”。上學的小孩經常在他家門口聚集,聽著笑話,以至於遲到。在那個謝村人以笑話為恥的年代,這位老漢為流傳的“謝村72掙”笑話“正名”,曾告訴他們,這是和孫悟空72變一樣的好東西。
如今,隨著經濟中心轉移和城鎮化程序,謝村變得安靜,柳槐樹被圍欄保護起來。冬天尤其安靜。
近10年的社會生活,在口口相傳的萬榮笑話段子中,幾乎是一片空白。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王旭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這並不奇怪,萬榮笑話作為一種民間口頭文學,產生的背景就是鄉土社會、熟人社會,之所以成為一種“遺產”,也是因為那種生活流失了。她說,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有一個理念,不再強調它(這種文化)是偉大的優秀的,而是強調它對於當地人生活的意義。
王旭2014年來到謝村做博士論文調研,當地人帶她來到“懶漢坡”,是過去村民去地裡勞動的必經之路、三岔路口,很多笑話在這裡發生,村民勞動之餘,也常常在這聚集“諞”笑話。但這種場景也成為歷史。
笑話在變化
大約2011年後,萬榮笑話逐漸進入發展的平靜期。鄉土之外,還有喜劇。太原的80後脫口秀演員徐飛常線上下演出,他觀察,本地線下脫口秀演出中,鄉土話題很少。
新時代的流行笑話屬於都市。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資料,2024年,在小劇場和新空間演出中,脫口秀(單口喜劇)演出場次和票房上升幅度最大,分別上升53%和48%。《笑在生長》這本書中,復旦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崔迪說,脫口秀的內容和背後的價值觀都具有明顯的都市性。
笑果文化創始人葉烽則分析:“相聲以前為什麼過不了長江?二人轉為什麼出不了山海關?因為背景和語境不同,因為笑點的產生是基於人們的共同認知。”“現在,為什麼脫口秀從南到北都可以?因為網際網路時代拉平了語言體系、拉平了語境。”
萬榮縣委宣傳部副部長袁國欽也聽著笑話長大。有一天,他看著央視播放的唐朝詩人紀錄片,想到:萬榮笑話就和唐詩宋詞元曲一樣,都是特定時期的產物。“適合當時那個笑話醞釀的土壤應當是比較淡薄了吧,或者是笑話過去,笑話又迎來了新時代。”

2月25日,李秀霞在直播間和粉絲打招呼。郭玉潔/攝
參加萬榮笑話劇表演的李秀霞40多歲,2019年之前,當地笑話藝術團每年都有一個多月下鄉演出,後來活動越來越少。她找了別的謀生路子,現在在網上賣駝奶粉。她的短影片賬號以萬榮笑話劇中的角色命名,堅持每天晚上8點直播。但是,這更像是一場典型的帶貨直播,彈幕裡偶爾有人說:講個笑話。講笑話和唱戲,是這場帶貨直播的調劑。
2023年,萬榮縣委宣傳部和文旅局在縣城辦了一場笑話比賽,希望能發現新的人才,但結果不理想,報名不算踴躍,段子內容也老套。萬榮縣上一次舉辦這種笑話比賽還是2000年年初。袁國欽能理解這種現實,“現在辦唐詩大賽,能辦得過唐朝嗎?”
這場笑話比賽,謝村的薛兩省被熟人拉著,懷著“熱鬧熱鬧”的心情去了。非遺傳承人王新棟臨時被拉去參賽,想了一個愛人告訴他的故事。一個賣筐子的農民,總是喊著這樣的叫賣口號:三八二十三。指的是3個筐子賣23元。很多人覺得他傻,笑他,傳開了,久而久之,很多人便被吸引過來,買他的筐子。一次有人問他,你是不是不會算數?老漢說:“三八二十三,你別把我當憨憨,我為多賣貨,你為少掏錢。”這則笑話被評委認為是典型的萬榮笑話,來源於生活,且包含著萬榮人的氣質,大智若愚。但在萬榮之外,這難說是一個能引起大笑的喜劇。
王新棟回憶起一個萬榮笑話的巔峰時刻。當時,兩位萬榮笑話的當地明星在同一天登上央視的兩個節目。很多人守著電視看。但王新棟記得,他有點失望。“用萬榮方言講出來才非常可笑。”“不土不洋的”,情節也不是那麼好笑了。
徐飛看了一些萬榮笑話段子,“大部分感覺都笑不出來,共情的少”。另一位生長在山西的脫口秀演員張煜是個00後。她說,她發覺自己與上一輩人在喜劇上的審美差異是,父母更喜歡看那些身邊的、熟悉的故事,而她更喜歡看各行各業的人講自己的生活,新奇的、新鮮的。她從去年開始講脫口秀,一次帶父母去看現場,父母說,“挺好的,只是我們老了。”

2月23日,萬榮笑話非遺傳承人解放葬禮上,樂隊在等待表演。郭玉潔/攝
但她也覺得,喜劇總歸是相似的,喜劇是一個“烏托邦”。她喜歡即興喜劇,其中有個重要概念是“YES AND”,即,無論一人說些什麼莫名其妙、光怪陸離的想法,搭檔都會順著這個設定往下說,“沒關係”。中學時她經歷過校園霸凌,也是那時愛上喜劇,“我只要大聲笑,所有的煩惱都可以忘掉。”
她覺得,萬榮笑話中最難得的,是它所昭示的那種生活方式,以幽默化解問題。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現在脫口秀何嘗又不是一種……對於他們(的)那種傳承方式呢?”
“我們的演出沒有託”
2025年2月下旬,和萬榮笑話有關的人們,因為一場葬禮見面了。萬榮笑話唯一一位國家級傳承人解放去世了,享年90歲。在大家記憶中,這是一位頗有老派知識分子風骨的老人,做記者、編輯,修志,一輩子清貧、認真。他不太會講笑話,但是第一個大膽將民間笑話寫入縣誌的人。
白紙上寫的悼詞裡,寫著他對笑話發展的貢獻。“笑話刊印發行廣,萬榮精神掙發揚。”葬禮上,民俗表演大約持續了兩小時。村中的助葬樂隊之後,是逝者家屬請來的非遺表演樂隊,表演中鼓聲和嗩吶聲震天,唱關於黃河的歌謠。在萬榮一些黃河邊的村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只是字面含義。黃河的多次改道,帶來多次洪水氾濫。但這樣的事也能被講在某個笑話的“鋪墊”中——黃河發了大水,靠河灘幾個村的人,爭先恐後下河撈炭、撈木料、豬羊、騾馬。
葬禮上,村裡的老人孩子聚集在一起。一群老人在牆根曬太陽,小孩們到處奔跑。男人們聚在一起互相遞煙,笑著。一位村民說,現在大家聚在一起閒聊的機會也少了。宴席上,郭澄和朋友們又講起笑話。郭澄說,面對生死,最好的狀態是:“快快樂樂活著,利利灑灑走著。”
他說,中學時學課文,讀過魯迅的《阿Q正傳》,覺得這是在諷刺中國人的性格。如今他60多歲了,卻感覺阿Q精神也不能丟。“(如果)一個200斤的人打你50斤的人,又能怎麼辦?”他說。

萬榮笑話起源地謝村附近的飯店,開了約20年。郭玉潔/攝
“只要把這個思想‘圓’了就行了。”生活中,兒女學習不好,沒找到好工作,他慶幸他們離家近,如果有出息,那就是“給國家培養的”。遇到委屈的事,他吃點小虧調侃過去,“你還能跟人家打官司呀?”
他說自己性格不強勢。“這些坎兒,透過笑話、笑料,自嘲,把心態調整好,自己不生氣,不生氣不得病,就健康,平安。”他說。
年輕的脫口秀演員張煜也從萬榮笑話中看到當地人“接受現實、擁抱現實的一種自由”。她說,這不是權利或義務,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獨特的自由”。
在萬榮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講笑話的人越來越少。但喜劇還存在於一些人心裡。2023年的笑話比賽,醫生黃泰從熟人那聽說了,他報名參賽。第一次表演效果不好,他不服氣,去請教評委,又上去重新講了一次,最後進入複賽。他可以背誦出馬三立經典相聲《相聲的魅力》的所有臺詞。尤其是那段多次重複的對白:“相聲就有這麼大作用?”“這有啥啊,相聲的作用大著呢!”
這幾年,電影放映員郭澄開始在短影片平臺拍攝自己新講的笑話。沒什麼收入,他嘗試接過廣告,又因影片時長達不到平臺要求作罷。“愛好。”笑話從生活變成事業,最後又回到生活。他把朋友牛娃編進笑話,形成“牛娃”系列。手機上,他記錄著那些寫笑話的靈感,100多條了。最近的一條靈感中,他寫道: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些晚會為了節目效果,專門安排了一些人拍手“大笑”,一種新型職業——託!
郭澄給這條備忘錄起的標題是——“我們的演出沒有託”。
– END –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