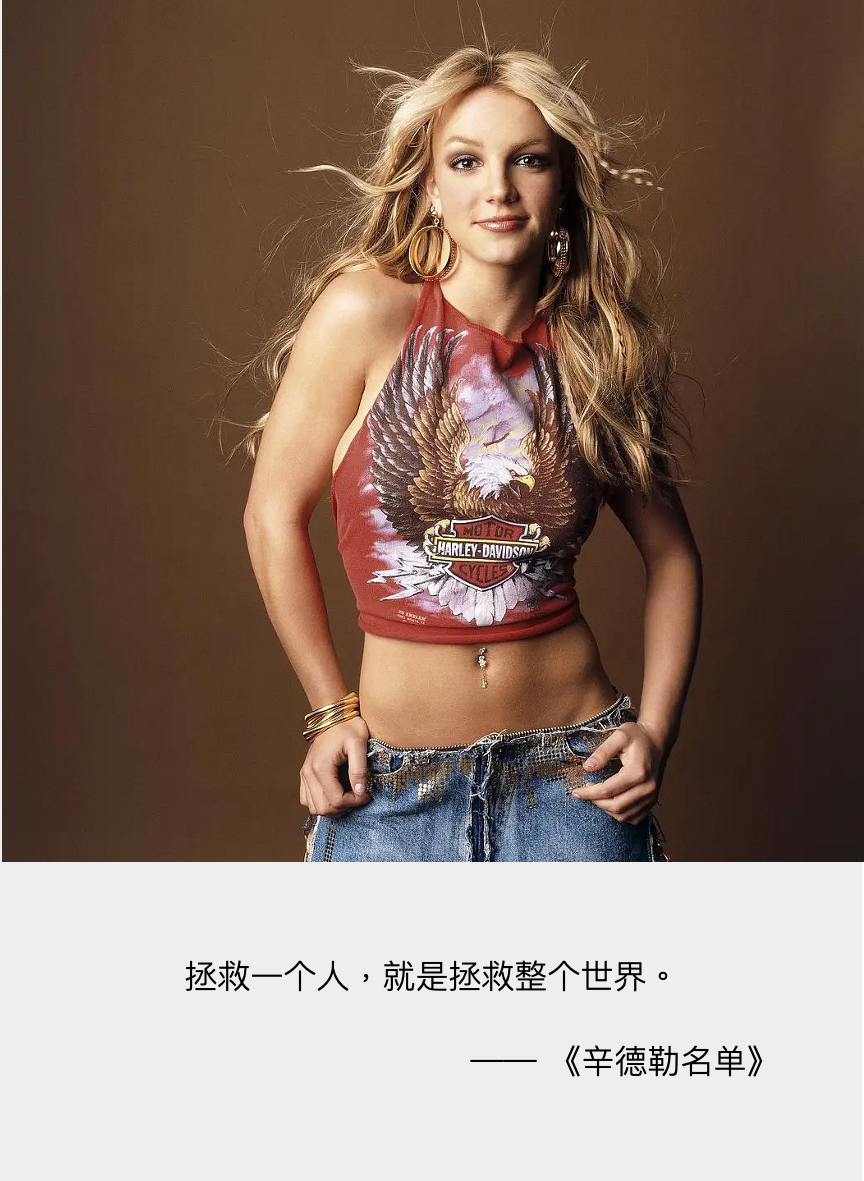㊟展覽現場
從你心中抽出的線織布做衣,彷彿你所愛的人將要來穿。/紀伯倫《論勞作》
花了近 30 年積攢下的碎布頭,已經 150 歲的老衣服,九旬老人口中用了一萬年的被子……上個月,服裝設計品牌“布言布語”把它們都搬到了單向街書店·東京銀座店。
置身於書店二樓的展覽和沙龍現場,這些來自深山手作的織物們展示著古老的生活方式,時間和指尖的溫度留下痕跡,在每一件成衣或布片上留下實體的情感。

㊟何燕兒在展覽現場
“布言布語”今年已經 29 歲,創始人何燕兒將自己稱為“做衣服的人”,會為客人修補穿著多年的衣服,從不按春夏秋冬的時裝標準來發布新款。
現代社會讓許多堅固的事物消散。當象徵祝福的“百家衣”消失,計算機不斷強調“補丁”的另一種概念,“布言布語”還在年復一年地回收邊角料,尋找重新利用的可能;他們探訪遠藏深山的年邁手藝人,邀請他們重新啟用古老的技藝。
這是何燕兒首次向海外介紹“布言布語”的服飾,在沙龍現場,她還分享了醞釀多年的“Mengji Nongga”系列:這是一句來自貴州少數民族的方言,意為「回家吃飯」。
從女性長輩那裡傳承而來的技藝,織物中流傳的精神信仰——美的感召跨越了代際,何燕兒和策展人高煜分別講述了布與時間、布與人、布與靈的故事,以及器物中留存的關於迴歸的召喚。

#布的故事裡有一種歸屬感
「Asian Talk 034 Mengji Nongga 回家吃飯」沙龍回顧
嘉賓/何燕兒(布言布語創始人)、高煜(策展人)
01
她們都是我的“外婆”
何燕兒(布言布語創始人):我做衣服其實有一個淵源。在我童年的時候,我外婆是一個很有名的能幹的婦女,我就記得她不停地在做東西,做衣服做鞋子,尤其是看到她年輕時候繡的枕頭頂、繡的鞋子,太驚歎了,這麼精細這麼美。

㊟沙龍現場
我一直守著外婆,看她做手針活,記住她所有的動作,一針一線地穿梭,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很痴迷。等我可以去動針線的時候,我的所有的動作就是復刻了我外婆的動作。
1993 年,我在中央工藝美院學習服裝設計。有一堂課是少數民族服飾欣賞課,其中有一條少數民族的裙子。當時我看到那個裙子,我就想怎麼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看的裙子,展開以後是一個大大的圓,有很多很多的褶皺,好像自然裡面美好的顏色都在那條裙子上。
那條裙子就是照見了我的內心的渴望,好像是一種召喚。
1996 年我去廣西,走的那條線路是苗族、侗族聚居的地方,非常原始,一路走一路看,看到他們的服飾,看到他們的木屋,看到他們勞作,各種節日都那麼盛大。她們織的佈讓我很喜歡,她們也願意把好的東西給我看。
在服飾的圖案裡面,是他們的歷史和文化。每個人的血脈裡面都有我們的祖先,都有這樣的記憶,不論是手的記憶,還是大腦的記憶。
在貴州有一句苗語,Mengji Nongga,是“回家吃飯”的意思。Mengji 是回家,Nongga 是吃飯。不論走到哪裡,“回家吃飯”都是我最熟悉的聲音。
曾經的那種記憶,帶著這樣溫度的衣服或者是生活用品,這種製作也叫 Mengji Nongga,這個品牌也是這樣一點一點地生出來的。在過程中,慢慢地成為了它應該成為的樣子,只是需要很沉靜的狀態去做這一切。

㊟沙龍現場
Mengji Nongga 這個品牌的出現,我會很不自覺地和我的外婆勾聯上,慢慢追溯到外婆的外婆。這樣的記憶,這樣的血脈傳遞、基因傳遞,我會找到更遠。我外婆的外婆可能和苗族有一個共同的祖先,我們是同一個源頭。
所以當我去到貴州,這種非常原始、非常古樸的地方,我就會發現她們都是我的“外婆”,會有一種回家的聲音在召喚,回到最清淨的地方,最初始的地方,最源頭的地方。
做衣服做到 30 年左右的時候,我就是被這種強烈的感覺召喚,讓我重新去思考做衣服這件事。

㊟何燕兒兒時的衣服
我為什麼要做衣服?其實應該從這件小衣服開始。這件衣服是我出生的時候我外婆給我做的,距現在是六十年。這個小孩是我,那是我的媽媽,這是外婆,這個是外婆的媽媽,外婆的外婆。這些照片從媽媽那傳給我,我在家裡就把這個照片按照順序裝在一個相框裡面。
02
這個被子已經用了一萬年
何燕兒(布言布語創始人):介紹一下我們上海的一個店鋪,在同仁路上。這個店鋪的外觀的是有尖頂的,內部結構也有幾個同樣的尖頂,構成了這樣的自然的、像部落一樣的,有這樣的家的氣息。
這個店鋪把布言布語和 Mengji Nongga放在一起。有的時候我自己也分不清做出的衣服應該是布言布語,還是 Mengji Nongga。

㊟布言布語上海店
後來我就這樣區分,有貴州的少數民族的婦女參與的,這樣的很慢的、更加慢的,帶著傳統手工藝的製作,就歸到 Mengji Nongga。
這是我們做衣服的工作室的日常,每件衣服一定要有手工的成分在裡面,就是釦子、手工釘、釦眼兒,手工鎖,我們沒有那個機械的鎖釦眼兒的機器。所以我們的扣子是衣服穿爛了,它也不會掉的。即使很現代的設計,也要用最傳統的方式去做,就像釀酒一樣。
它需要時間來發現。需要手的溫度注入到衣服裡面。
這位老人已經九十六歲,這個是她的被子。她結婚的時候,她的媽媽沒有什麼送,就送這樣的被子,補了又補、補了又補的被子。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因為世世代代的衣服都在裡面。
然後我問這個被子已經用了多少年了,她們說一萬年。因為她們不知道有多少年,她覺得一萬年就是很久很久。
但這些被子的結果是會被燒掉。因為年輕人不會再住這個木屋了,他們會建成水泥房。他們覺得這個被子又髒又破,沒有面子,就會把它燒掉。


㊟老人和“一萬年”的被子
我像寶貝一樣地把它帶回家,然後去洗、去清理,從上面清洗下來很小很小的一批料,然後做成了這些展品。
那個小布已經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再讓老人幫我縫在上面,這些都是老人做的。
我們從 1994 年開始做衣服,到現在所有的面料的碎料廢料都會報給我,然後我們把這些面料進行再設計。這邊的衣服,還有那邊織的布,全部都是用這種碎布設計的。這些衣服都是帶著這樣的風格,帶著這樣的情感。
這是我收藏的一段話,《論勞作》——
我們怎樣才是滿懷仁愛地勞作呢?
那就是用從你心中抽出的線織布做衣,彷彿你所愛的人將要來穿。
那就是滿懷熱情地建造房屋,彷彿你所愛的人將要來住。
那就是滿懷溫情地播種,歡天喜地地收穫,彷彿你所愛的人將要來吃。
那就是把你心靈的氣息灌輸到你所製作的一切之中去。

㊟妹爸,55 歲,在用竹子編織馬尾斗笠

㊟妹媽,52 歲,手裡拿著她的勞動所得
她從 2008 年開始織布

㊟這一個墊子差不多要編一年的時間

㊟更多參與了織布和染色的少數民族婦女
03
布料裡有對神明的敬仰
有對祖先的懷念
高煜(策展人):我會開始接觸到織物,其實也是和我媽媽做的苗族收藏有關係,然後是阿城老師寫的一本書,叫《洛書河圖》。
他在裡邊把苗族刺繡的部分和青銅器進行了對照,然後又從這個太極裡面推出了八角星的圖案——這個八角星的圖案也大量分佈在苗族的服飾上。他的結論是,中華民族的源頭有可能還儲存在貴州的這些衣物上。
織物的起源是什麼?比如西方說亞當和夏娃是為了遮羞,才用衣服來遮來遮蔽身體,東方會說有避寒的需求,那是不是還有第三種可能性呢?

㊟沙龍現場
當我走過太平洋這些小島之後,我覺得織物可能不完全是為了遮羞或避寒而做的。
這些小島上的部族依然保持著傳統,其實他們並沒有遮羞的必要,也沒有禦寒的需求。他們這多數的地方都相信萬物有靈官,穿著衣服也完全是為了儀式,為了去和神靈溝通。
大概是在 2015 年的時候,我去到印尼的弗洛勒斯島。我和他們一起去出海,一起去打漁,在他們的船上發現了這樣的一塊布,很長很長,大概有 8.3 米。
他們在暴風雨來的時候,就會把自己裹在這個布里邊,然後祈求自己能安全地回到家鄉、回到岸邊。這個布上邊會有一些祖先和船的圖案,保佑他們能平安歸來。這塊長布也是由這個村子裡邊的所有婦女,為她們的丈夫安全歸來去做的。


㊟弗羅勒斯島的船布
這塊布是我收藏的開始,我對它的技法、來歷和用途非常感興趣。
在我收集船布的這個島上,我發現很多年輕女性會穿著一種叫拉烏布圖的筒裙跳舞。這些筒裙,其實只有村寨裡頭地位最高的女性才有資格穿著它,但是地位最高的女性不一定是年長的,而是年輕的、生育能力強的,這主要是跟生殖崇拜有關聯。
但現在的情況是它們在每一個村寨只有一個,因為做這個的人越來越少了。

㊟叫拉烏布圖的筒裙
接下來是在蘇拉威西島,這個島上的葬禮非常有名。他們的葬禮很繁瑣,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需要宰殺大量的牲畜。我們 2018 年去採訪一家人的時候,這家的媽媽去世了,因為她的地位很高,就需要宰殺二三十頭的牛,每一頭要七萬到八萬人民幣。
他們會用這樣的布來包裹屍體,這個屍體會被存在家中,等到攢夠了錢才能去辦葬禮。這個布料上會有一些勾連的圖案,有人解釋說它像祖先的手,來招呼這個新的王者加入祖先的行列,加入可以被崇敬的行列。
他們會認為人死了是一種比較特殊的病,只會不會說話了而已。只有當這個人舉行了葬禮,舉行了社會性的儀式之後,這個人才能被真正地接納到祖先的行列裡。
因為要攢夠很多很多很多的錢,這個過程大概要三四年、五六年。所以他們會定時清洗、更換這個衣服,包裹在逝去的人的身體上。然後他們那邊有比較特殊的防腐機制,就像木乃伊一樣,氣味也不會很臭。
這樣的布也會對我的生與死的觀念產生影響,它會拓展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蘇拉威西島的布
然後接下來到婆羅洲,他們比較有名的是關於獵頭的習俗,大概在 1920 年都還存在。
男性要去獵頭,女性就要製作這樣的織物。女性在製作這樣的布的時候,她需要進入一個通靈的狀態,在一個小屋裡頭自己待三天到四天,不吃不喝,才能接受所謂神的啟示,把圖案織成布。
她織成這樣的布所獲得的榮耀,和男性去獵頭所獲得的榮耀其實是相等的。而且女性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也是很危險的,因為她要在精神的領域裡面去和不好的東西搏鬥,可能會產生精神方面的疾病,很危險。

㊟獵頭的圖案
像我之前介紹的這些布料,它其實是有很強的精神力量在裡面。大家會把精神、對神明的敬仰、對祖先的懷念都傾注到這個布料裡面。這些布料也會反哺回製作的過程本身,帶來護佑的力量。
這種由布產生的靈、由布產生的這種歸屬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想最後用費孝通老師的這一句話來結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沙龍現場
它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去欣賞與我們自身相關聯的美,也可以去欣賞他人之美。這句話就點醒我,這兩種美之間是共通的,我們最後可以達到天下大同、天下是一家的概念。
我認為這個美,其實和 Mengji Nongga“回家吃飯”的這個“家”是一個概念,這個家不一定是一個實體,它可能是精神上的這種歸屬感,有安心的感覺。這個家它也是美,“回家吃飯”,就是回到這個美的地方來。
所以我發現我和我媽媽所做的東西是有共通之處的。與其說是我受到了家族的感召,不如說其實我們都是受到了布的感召,向一個方向一直往前走。
攝影:IKEN火車
編輯:豬猛猛
監製:李二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