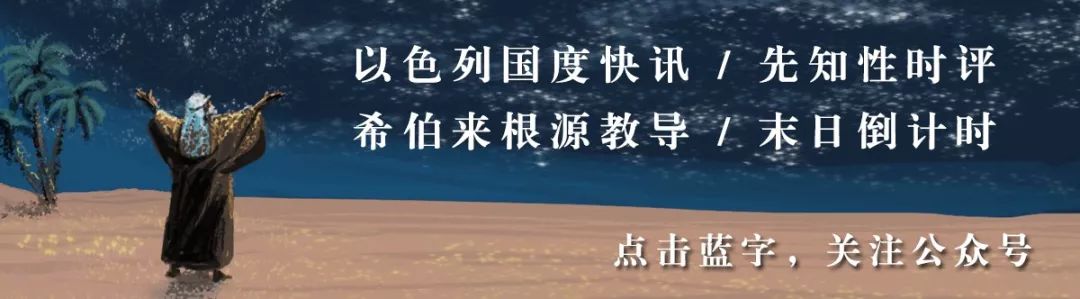“別放棄聽音樂,特別是聽埃拉·菲茨傑拉德唱的歌。”
文丨特約作者 姜乙
最難忘的收聽埃拉·菲茨傑拉德(Ella Fitzgerald)的經歷,要追溯到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那天,我在學長家再次聽到他對這位偉大歌手,或對整個爵士樂滔滔不絕的讚歎。作為一位深邃的爵士樂愛好者,他的語氣往往超乎想象:
“爵士樂就像建築,像生活內部看不見的網,像超級大都會的組織體系。它將我們從所在之處,從我們熟知的世界中解放出來。它告訴我們事物的全部 , 而不是對和錯。一切事物的微妙與豐富之處,光說對和錯是不夠的。怎麼說哪,城市的白天就像在哭或像個啞巴,但在夜晚,或許每盞燈下都有人在跳舞。而埃拉,該怎麼形容這位女士?當號角在黃色的燈光下閃爍著金色的光,閉上眼睛,當希望的魔法出現,幸福又如此難以把握,思緒靜止或改變方向,當內心的波瀾變得平靜或被重組——當我們被深深打動,那是埃拉的歌聲!”
一段絕妙的表達後,他揚起漂亮的左手,又不自覺抬起頭,像是在質樸而虔誠地仰望著什麼——不可思議,不是嗎?不過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他擅長用語言表達他無論是在聽爵士樂時,還是在聽古典樂時的沉思,而每一位深愛爵士樂的人,都會在某個被 “深深打動” 的時刻,試圖說出幾句翻騰在內心的肺腑之言。這就是爵士樂的魔力。它的每個樂句中,每次跌宕的輾轉間,都潛伏著一個撩撥心絃的小精靈。
當然,那天,學長也表現出我所不熟悉的一面。與以往不同,我們聽了些埃拉演唱的 “童謠”。那張專輯叫《埃拉小姐的遊樂屋》(Miss Ellas Playhouse)。在那樣的歌聲裡,我的學長吃著餅乾,笑著,說著,餅乾渣掉在他的毛衣上,他跟著音樂情不自禁地、快樂地搖擺身體,似乎到了忘我的境界。儘管我們一直以來的共同感受是,埃拉是個深不可測的人物。她負重前行,卻總能表現得無比輕盈,比起我們同樣熱愛的令人心碎的比利·哈樂黛(Billie Holiday)小姐,她更加撲簌迷離。但誰能招架得住她此刻散發的天真氣息呢?
那是個難忘的下午。是啊,幸福如此難以把握。我回味著學長的話。世界上真有幸福這回事嗎?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們往往陷入溫柔的沉默,但聽到埃拉的歌聲,我們又總是一邊體會她渾身上下的每個細胞都為創造妙趣而生的天分,一邊在她的歌聲中,在她表現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細節和具有無窮創造力的即興節奏中、旋律中,微笑著隱約感知了幸福的含義。
“如果她用歌聲講了一個故事,你得記著,她剛才講的那個故事裡,至少還有一個故事。” 他笑著說。

那天,我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叫《提斯克-塔斯克》(A Tisket- A Tasket)。這首歌最早記錄在 19 世紀末的美國童謠中,旋律在其他歌中也反覆出現。諸如配上 “下雨了,下大雨了”“雨雨走開” 或 “圍著羅西轉” 之類的詞。而 1879 年它首次出現時,唱的是一種古老的遊戲:孩子們圍成一圈跳舞,其中一個跑到圈外,丟下一塊手絹,隨後離他最近的孩子要撿起手絹,並追逐丟手絹的人。如果被抓住,丟手絹的人要麼被親吻,要麼必須說出心上人的名字。埃拉的歌聲激越、頑皮,“我的小黃籃子丟了,如果那個女孩不還給我,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活潑地唱著,歌聲觸碰了房間裡的每樣東西,又在空氣中瘋狂打轉,如此迅捷自由!那個小籃子,似乎成了快樂本身。
還有一首叫《鬆餅人》(The Muffin Man)的歌同樣令人難忘。唱的是 “鬆餅人” 如何不急不躁、無憂無慮地工作的事。這個人住在倫敦的德魯里巷,可能是個送鬆餅上門的小販。“你認識鬆餅人嗎?” 埃拉熱情地唱道,“是的,我認識鬆餅人!” 這種對話的建構散發的輕鬆幽默,令人愜意無比。旋即,埃拉機趣地開始了即興演唱:“你認識賣冰激凌的嗎?你認識擺水果攤的嗎?”“是的是的,我認識!” 這些人在埃拉的歌聲中成了快樂、善良和慷慨的象徵,他們在德魯里巷的出現,隱喻了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個小小的奇蹟。埃拉對《鬆餅人》的演繹,提醒我們暫停、反思、觀察和享受生活。
“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一天,我是說真的!” 回憶起那天和那天的爵士樂,我不禁笑起來,又想起傑夫·戴爾的《然而,很美》(But Beautiful: A Book About Jazz)中的這句話。
埃拉·菲茨傑拉德與她的同行比莉·哈樂黛的確不同。後者以悲劇故事吸引聽眾,埃拉則主要傳達她對生活的熱情。儘管與大她兩歲的比莉一樣,她也經歷了黑暗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埃拉幾乎不認識自己的父親,又受到繼父的虐待,14 歲失去母親,從弗吉尼亞州的家中逃到紐約。在那裡,她曾一度流落街頭,在妓院放哨,給賭徒當幫手,與警察打交道是家常便飯。
隨後,少年法庭將她送進了一家女子勞改所,不久後她又從那裡逃出來。大蕭條時期,一個無家可歸的黑人女孩,在感化院受盡了折磨。但與比莉·哈樂黛不同的是,埃拉·菲茨傑拉德從未染上毒癮和酒癮,也很少談及自己的艱辛往事。1934 年 11 月 21 日,埃拉參加了哈萊姆區阿波羅劇院舉辦的選秀節目。她喜歡跳舞,本來想跳舞,卻被比賽嚇倒了,雙腿軟得像布丁,怯場症牢牢地抓住了她,觀眾開始躁動不安。這時埃拉自發地唱起了霍奇·卡邁克爾(Hoagy Carmichael)的歌曲《朱迪》(Jude)和博斯韋爾姐妹(Boswell Sisters)的《我的摯愛》(The Object of My Affection)。她猶豫著開始演唱,管絃樂隊慢慢跟進來,她變得越來越自信。最後,17 歲的埃拉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遇到了自己的命運。
說到一位歌手站在舞臺上必要的勇氣和自信,我又想起自己經歷的有趣往事。那時,我的老師總是對我無可奈何,稱我 “糯米糰子”。意思是對於舞臺,我太過怯懦了,幾乎毫無光彩。我那時確實非常迷茫,上了音樂學院後,上臺對我來說變成了可怕的審判。究其原因——我想,或許是我無法接受自己是個花腔女高音這一判定。我不僅覺得自己的歌聲變得像雞叫,還要努力說服身上那個執拗倔強的人,極力扮演各種輕佻的小姑娘。
我記得有一次是期末考試前的走臺,音樂廳裡稀稀拉拉坐著十幾位同學,他們來自不同的系別,閒聊著,漫不經心地充當著最挑剔的評論家角色。我的老師要我上去,唱一遍次日考試的曲目,古諾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裡朱麗葉的詠歎調《我想活在這夢境裡》。我一邊唱,一邊在老師的不滿和批評聲中,站在臺上絕望地哭起來。
還有一件小事記憶猶新。那天是老師的生日,我們去她家慶祝。吃過蛋糕後,我們一起看普契尼的《波西米亞人》。那是一部歌劇電影,最後唱起了《咪咪告別》。我實在忍耐不住感動的淚水,又似乎在極力維護某種木訥的形象,兩廂交戰中,我還是不爭氣地哭出來。
這時我的老師扭過頭:“你在哭嗎?” 她一把抱住我,“你是有感情的,糯米糰子,你還有希望!” 這時,我又想起我身上那個不被理解的人,哭得更厲害了。
學長說得沒錯:“唱不好或不愛唱時,多讀譜,不過什麼都不做也行。別放棄聽音樂,特別是聽埃拉·菲茨傑拉德唱的歌。” 轉身離去時,他又熱切地補充道:“你也將遇到你的命運。Lady,Be Good![1]”
那個 17 歲初次登臺的小女孩埃拉·菲茨傑拉德後來成了爵士樂最偉大的詮釋者。她在舞臺上活躍了近六十年。她以靈活的嗓音和如同即興演奏某件樂器般流暢的聲音線條聞名於世。幾乎沒有哪位歌唱家能像埃拉一樣,將作曲家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科爾·波特(Cole Porter)、歐文·柏林(Irving Berlin)和傑羅姆·克恩(Jerome Kern)譜寫的歌曲演唱得如此婉轉細膩——歌詞在她口中融化,在她長長的呼吸上翱翔。她的歌聲既像個孩子,又像位母親。她的高音閃閃發光又輕而易舉。1980 年,她已幾近失明。在漢堡的一場音樂會上,在攝影師的閃光燈中,她幽默地即興唱起了《閃光燈刺痛了我的眼睛》(Flashlights, hurting my eyes)。1991 年,埃拉·菲茨傑拉德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辦了最後一場音樂會,五年後在病痛中去世。她活到 79 歲。

在埃拉的歌聲陪伴中,我度過了艱難的求學歲月。日後沒有從事與音樂相關的工作,不會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那些磨礪讓我理解了自己,瞭解了自己的限度,教會了我在茫然中欣然接受自己。儘管在某些時刻,我仍夢想著能像埃拉一樣在舞臺上揮汗如雨、賣弄風情,但那不過是個無需實現的甜夢罷了,對的,那個夢成了我心中的一顆蜜糖。這顆蜜糖在我聽到埃拉的歌聲時,或回憶往事時,散發出奇異的甜蜜芬芳。它一再激勵我煥發新一輪的熱情,告訴我,埃拉所深信的事,不僅是成為最偉大的爵士歌手,更是在生命中輕盈地跳舞,無論順境逆境。我不想刁難自己,而是想像埃拉唱的 “鬆餅人” 一樣,不急不躁、無憂無慮地去發掘生活中的小事蘊含的意義,在音樂中,在埃拉的歌聲中,度過一個個 “最棒的一天”。
還是學長說得好:“當音樂響起,當埃拉開口歌唱,那簡直是為冷漠的修辭上的最棒的一課。誰都聽得出,埃拉深信著某些東西。那是她巨大的音樂智慧。”
窗外的夜晚閃爍著霓虹燈。我拿出一張唱片,埃拉的唱片。當音樂響起,當埃拉從容地開口唱道:
你是鬥獸場
你是盧浮宮
你是施特勞斯的旋律
你是班德爾牌的女帽
你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你是米老鼠 (喵嗚)
你是尼羅河
你是比薩斜塔
你是蒙娜麗莎的微笑
你是聖雄甘地
你是拿破崙白蘭地
你是西班牙夏夜的紫光
你是國家美術館
你是葛麗泰·嘉寶的片酬
你是賽璐玢
你是火雞盛宴
你是賽馬冠軍的獲勝時刻
你是華道夫沙拉
你是《柏林敘事曲》
你是弗雷德·阿斯泰爾靈活的舞步
你是尤金·奧尼爾的戲劇
你是《惠斯勒的母親》
你是卡芒貝爾乳酪
你是玫瑰
你是穿越地獄的但丁
你是吉米·杜蘭特的鼻子
……[2]
我被她的幽默征服了,不禁笑起來,並在心裡默默地、虔誠地說:You are the Top,埃拉,我讚美你!
作者推薦:
埃拉·菲茨傑拉德在爵士樂歷史上堪稱經典的五張唱片。
ELLA FITZGERALD SINGS THE COLE PORTER SONGBOOK, 1956

Verve 唱片公司 1956 年首次發行的這些錄音,呈現了一對最佳組合。作曲家科爾·波特,具有諷刺意味的歌詞與和聲創作的大師,和擁有迷人嗓音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清晰吐字的埃拉·菲茨傑拉德。歌唱家在這樣的句子中塑造母音和子音的方式令人如痴如醉:“鳥兒尋找伴侶,蜜蜂在配對,甚至圈養過的跳蚤都蠢蠢欲動,我們也在一起,我們也相愛吧。” 或者,她是如何讓下面的句子蕩氣迴腸的:“昔日,瞥見絲襪都讓人感到震驚。而今,天知道!一切都變了樣。” 或者,在歌曲《開始跳比津舞》(Begin the beguine)中,她又是如何毫不費力地攀登聲音的巔峰的。據說科爾·波特聽到錄音時,對這個 “小女孩” 的美妙發音驚歎不已。她唱出的每個字都是音樂,更美妙的是,她讓波特的旋律閃耀著優雅的光芒。
ELLA FITZGERALD & LOUIS ARMSTRONG: "PORGY AND BESS", 1957

喬治·格什溫的歌劇《波吉與貝絲》中的歌曲配上大型管絃樂隊的伴奏,以及兩位爵士樂巨星成熟圓潤的歌聲。1957 年,埃拉·菲茨傑拉德 40 歲,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年長 16 歲。路易斯沙啞的嗓音與埃拉天鵝絨般細膩的歌喉,在激烈而動人的聲樂對話中相得益彰。在羅素·加西亞(Russell Garcia)的編曲下,管絃樂隊的演奏既有力又精緻。《夏日時光》(Summertime)《未必如此》 (It Ain'T Necessarily So)和《貝絲,你現在是我的女人 》 (Bess, You Is My Woman Now)等絕對精彩的曲目讓人大飽耳福。粗獷的路易斯常常表現得異常脆弱,埃拉則柔情似水,深情款款。她在這張專輯中創造了令人驚奇的音色——以演唱靈歌的方式加上自然的搖擺,當然,她還順勢提高了兩個半八度的音調。
ELLA IN BERLIN: "MACK THE KNIFE", 1960

音樂史中的幾分鐘,就足以讓一位音樂家永載史冊。1960 年 2 月 13 日,當埃拉·菲茨傑拉德登上柏林的德國音樂廳的舞臺時,她就創造不朽。在演唱到《暗刀麥奇》(Mack the Knife)一曲的 1 分 42 秒時,她所做的一切,使她成為演唱爵士樂歌曲和即興表演的女王。從布萊希特 & 威爾(Bertolt Brecht & Kurt Weill)的經典作品的第四節開始,埃拉忘記了歌詞,於是她擺脫了文字,開始了瘋狂的即興演唱。僅僅五分鐘的《暗刀麥奇》之後,一個永恆的版本誕生了。這段錄音堪稱傳奇。1961 年,她憑藉這張專輯和她的即興演唱獲得了格萊美獎。1999 年,這張《埃拉在柏林》(Ella in Berlin)更是因其長盛不衰的品質和這件錄音作品具有的歷史意義而被評委會收入了格萊美名人堂。順便說一句,埃拉·菲茨傑拉德曾 13 次奪得格萊美獎,包括一項終身成就獎(1967 年)。
ELLA FITZGERALD & DUKE ELLINGTON ORCHESTRA: "ELLA AT DUKE'S PLACE", 1965

1957 年,埃拉·菲茨傑拉德首次與她崇拜的艾靈頓公爵合作,將他的作品錄製成四張 “Song Book” 唱片。在此基礎上,她於 1965 年與艾靈頓及其樂隊花了一個下午錄製了這張專輯《埃拉在公爵之家》(Ella at Duke's Place)。在這張專輯中,輕鬆的節奏佔據了主導地位,只有最後的比波普名曲《棉尾兔》(Cotton Tail)節奏加快。埃拉以一種愜意的方式演繹著這些充滿藝術氣息的歌曲。她自信的演唱、飽滿的音色以及在音符末端獨特的平顫音,再次成為營造艾靈頓公爵和比利·斯特拉霍恩(Billy Strayhorn)作品氛圍的絕佳 “樂器”。她演唱的《熱情之花》(Passion Flower)和《花是迷人的東西》(A flower is a lovesome thing)令人陶醉,《天青》(Azure)則讓人浮想聯翩。
ELLA FITZGERALD/JOE PASS: "SPEAK LOVE", 1983

這張專輯是 1983 年埃拉·菲茨傑拉德與吉他手喬·帕斯在錄音室的合作。這對搭檔的第三張錄音室專輯散發出二人之間無比默契的氣息,但同時,又充滿了冒險精神。在《女孩聊天》(Girl talk)中,65 歲的埃拉像個少女。在《心繫喬治亞》(Georgia on my mind)中,她又像個靈歌女王。在搖擺的《我也許錯了,但我認為你很棒》(I may be wrong, but I think you're wonderful) 中,她的歌聲無限柔美,充滿調情和調侃的意味。喬·帕斯可能是爵士樂史上技術最精湛的吉他手了。他的彈奏令人回味無窮,時隱時現,並始終以他對歌聲的感受做出即興的演奏。他們共同創造的聲音像大樂隊一樣令人震撼,在《輕言細語》(Speak Low)中,一切又保持了鬆弛。聆聽這張專輯的每一首歌都是一次享受。它是爵士樂室內樂中最好的專輯。
作者介紹:
姜乙,德語譯者。15 歲起學習聲樂,曾就讀於中國音樂學院歌劇系本科。譯有《悉達多》《人類群星閃耀時》《德米安》《西線無戰事》《荒原狼》及短篇小說若干。
題圖來源:JAZZ.FM 91
文內首圖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註釋:
[1] 美國作曲家喬治·格什溫(George Gershwin,1898-1937)創作的名曲《女士,好樣的!》。
[2] 唱的是 1934 年美國音樂家科爾·波特(Cole Porter,1891-1964)創作的音樂劇《萬事皆可》(Anything Goes)中最受歡迎的歌曲《你是最棒的》(You are the Top)。歌詞的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它濃縮了 1930 年代中期備受推崇的人事物。

《晚點 LatePost》推出週末版,希望把視線擴充套件到各種各樣的創造者。簡單來說,我們想知道誰在創造,並以之影響周邊;我們既注視當下,也回顧過去,尋找形塑今日世界的源頭;我們關注技術、商業,也關注歷史、人文,打量這些領域的交匯處的湧現。
讓我們關注的可能是一款產品、一家店鋪、一種包裝的設計思路,也可能是某種工作哲學、產品理念、管理方法,可能是一種有趣新穎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今天仍然煥發光彩的古老思想。
“已經創造出來的東西相比有待創造出來的東西,是微不足道的。” 這是維克多·雨果的話——我們希望《晚點》週末印證這句話。

·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