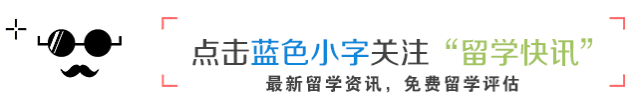▲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31日,美國猶他州,莊凱在郊外的一頂帳篷裡被安全找到。(視覺中國 / 圖)
全文共3583字,閱讀大約需要8分鐘
-
僅在澳大利亞,2020年,聯邦警察就收到了54起虛擬綁架案件報告,是2018年的兩倍有餘。
-
第三代虛擬綁架冒頭,與大資料時代有關:詐騙人員能夠更精準地提取受害人的個人資訊。
-
詐騙人員得手的關鍵在於設立資訊屏障,受害人則要嘗試反其道而行,適時中斷與詐騙人員的通訊,及時與親朋好友交流,或聯絡駐外使領館。
文|南方週末記者 姜博文
南方週末實習生 邵鎔 葉蕾蕾
責任編輯|譚暢
2023年年底,在美國猶他州,一樁令人費解的“綁架案”發生了。12月29日,警方宣佈,在裡弗代爾市一所高中學習的17歲中國交換生莊凱(音)失蹤。根據猶他州失蹤人員警報,警方相信“莊凱被從家中強行帶走,並在違背其意志的情況下遭到拘禁”。
然而,兩天後,警方在猶他州百翰市附近山區的森林裡找到了莊凱。被發現時,莊凱正待在一頂帳篷裡,雖然又冷又怕,但無生命危險,身邊亦無綁匪。
這起“綁架”最終被證明是一場詐騙。案中並沒有真正的綁架行為,詐騙人員先哄騙莊凱自行前往山區露營,隔斷他與外界的聯絡,爾後要求他拍攝自己看似遭到綁架的照片,營造假象;另一頭,他們聯絡莊凱在中國的父母,透過照片讓父母確信兒子遭到綁架,進而要求他們支付贖金。
作為傳統電信詐騙的變種之一,這樣的虛擬綁架並非新近出現的騙術。長期研究線上詐騙的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犯罪學在讀博士生周由發現,伴隨海外中國留學生數量不斷增加與越發嚴重的身份資訊盜竊,主要針對中國留學生的第三代虛擬詐騙案件數量正在上升;因案件通常涉及跨國犯罪,監管與打擊困難重重。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學院副教授李春勇建議,遏制此類犯罪,要堅持源頭治理。
兩頭騙
2024年1月3日,裡弗代爾市警察局局長凱西·沃倫在新聞釋出會上介紹了這起虛擬綁架案的全過程。
按照沃倫的說法,早在莊凱失蹤約一個月前,詐騙人員就透過電話聯絡上了莊凱。最初,他們以莊凱父母的人身安全為要挾,不斷要求莊凱給他們轉錢,否則就會傷害他父母。莊凱也照做了,“他相信他做這些事情,是為了保護他在中國的父母”。
但到了一定時候,不斷給兒子打錢的莊凱父母起了疑心。此時,詐騙人員轉變策略,走向了虛擬綁架。
2023年12月28日,裡弗代爾警方接到莊凱所在高中的報警。學校得知,莊凱的父母此前收到一張照片,照片中,兒子看起來的確是被綁架了。與此同時,“綁匪”也向他們勒索贖金。警方隨即前往莊凱的寄宿家庭調查,發現寄宿家庭並不知道莊凱已經失蹤,他們最後一次見到莊凱是在當天凌晨3點半。
裡弗代爾警方一面著手尋找莊凱,一面也開始尋求與郡警、聯邦調查局等機構合作。最終,透過追蹤莊凱過往手機訊號位置等方式,警方在2023年12月31日於百翰市的森林裡找到了莊凱。他是遵照了詐騙人員的指示,將自己隔離在了林區的一頂帳篷裡,還拍攝了自己“被綁”的照片。儘管莊凱並無性命之虞,但他的父母已經向詐騙人員支付了約8萬美元的“贖金”。
南方週末記者聯絡裡弗代爾市警察局,試圖獲知該起案件更多細節。裡弗代爾市警察局以目前所有案件資訊均可在網上查到為由,並未透露更多資訊。
34歲的周荃不是虛擬綁架的直接受害人,但目睹過一場與莊凱案極為相似的騙局。如今是一家公司經營者的她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2023年8月,她的一位朋友找到曾有海外留學經歷的她尋求幫助。朋友的孩子剛到澳大利亞留學,一天,朋友接到孩子的語音電話。電話那頭,一個陌生人的聲音響起,要求朋友準備100萬元,否則就撕票。
孩子的父母在國內報警,也聯絡澳洲的學校報警。周荃記得,報案當天,朋友就在微信上收到孩子嘴巴被塞毛巾、手腳被捆綁、臉上有血的照片。與此同時,一個影片電話打來,朋友接起後發現,影片中正是孩子被捆綁的樣子。隨即,又一個語音電話打來,對面再次強調,要在次日下午6點前收到100萬元,還發來了銀行賬號。
當時,同在現場的警方看了影片,認為不是真的綁架。周荃同步收到照片,看過後,她也發現了不對勁之處。“手腳是用電話線綁的,特別松,感覺隨時可以自己解脫出來,臉上的血顏色也不太對。”
周荃另外聯絡了一位在澳洲的朋友前往學校瞭解情況。好訊息很快傳來,出事第二天,澳洲警方就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孩子。周荃得知,這是一起騙局——詐騙人員以孩子父親給他留學的錢來路不正為由,要求孩子轉賬,並稱若不轉賬,其父會在國內被抓,孩子也會被澳洲警方抓捕。
從父母那裡要了幾十萬元轉賬後,孩子不敢再要錢,打算取出父親給他存的理財產品。銀行給父親去電詢問,父親不允許取出。失敗後,詐騙方告訴孩子,可以在宿舍以外找個地方,拿電話線綁自己,用番茄醬偽造血液,製造被綁架的假象。拍攝照片後,詐騙人員拿著照片向父母勒索錢財。雖說100萬元沒有騙到,但先期轉給詐騙人員的幾十萬已難追回。
“後面孩子說,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很相信詐騙(者)說的。那些人把他的資訊都瞭解得很清楚,說的資訊很多都很真,加上孩子剛到國外沒多久。”周荃回憶。

“虛擬綁架”套路多,中國駐外使領館釋出安全提醒。(視覺中國 / 圖)
大資料與新技術
2022年,周由開始撰寫一篇有關虛擬綁架的論文。他概括,虛擬綁架即騙子透過非接觸的方式虛構綁架情節以勒索贖金的一類網路詐騙。
虛擬綁架有其特殊之處。周由稱,他發現該領域過往文獻很少,但近年來相關案件數量激增。僅在澳大利亞,2020年,聯邦警察就收到了54起虛擬綁架案件報告,這個數字是2018年的兩倍有餘。
周由將虛擬綁架分為三代。從1990年代座機時代的虛擬綁架,到網際網路初期的虛擬綁架,再到如今的精準虛擬綁架,三十年過去,虛擬綁架的特徵亦隨時代而變。
周由發現,第三代虛擬綁架冒頭,與大資料時代有關:人們線上時間增加,資訊暴露的可能性變大,個人身份資訊盜竊與販賣亦開始產業化,詐騙人員能夠更為精準地提取受害人的家庭情況、住址、身份證號、電話號碼、姓名等資訊。
除此之外,根據多國警方披露的受害人資訊,第三代虛擬綁架也更多瞄準了中國留學生。周由分析,除了中國留學生群體本身數量龐大,相較於歐美國家的國民,中國人也被認為有更好的儲蓄習慣。
李春勇分析,此類案件中,詐騙人員會首先使用竊取、購買等各種手段蒐集受害人的資訊。隨後,他們利用公眾對於官方機構的信任,冒充公檢法機關或中國駐外使領館工作人員,誘騙受害人說其涉及某犯罪案件,要求其接受詢問、調查。“因為一旦涉及犯罪案件,受害人心裡才會高度緊張。”
使用此類話術“粘住”受害人後,詐騙人員一面利用心理恫嚇套取受害人家屬聯絡方式、護照資訊等更深層次資訊,一面要求受害人斷絕與外界的來往以便進行行為控制,例如要求受害人將手機暫時關閉、解除安裝社交軟體等,僅與詐騙人員單線聯絡。他們還會要求受害人離開居住地,到一個隱蔽且陌生的地方,防止受害人身邊有人識破騙局。最後,他們會使用受害人的照片或影片聯絡其家屬,勒索“贖金”。
除了兩頭騙,亦有受害人懷疑,這一代虛擬綁架已經開始運用新技術。一位在英國讀本科的19歲中國留學生就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23年11月,她在國內的母親曾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告訴母親,她的女兒被綁架了,一個與女兒很像的聲音也在那頭哭。來電者要求母親在30分鐘內湊齊50萬元,並加他的微信,每10分鐘截圖銀行卡餘額。母親希望與女兒視訊通話,對面答覆稱,如果她聯絡女兒,就立即撕票。
前述留學生回憶,結束通話電話後,母親很快報警,同時在英國時間早上6點半給她打了電話,才確認此為一場騙局。她懷疑,那個與自己聲音很相似的哭聲,是此前她接到無人說話的電話時被錄下了聲音,進而合成的。
受害人的脆弱與羞恥
近五年來,中、美、澳等多國警方均曾披露過虛擬綁架案例及詐騙人員的作案手法。然而,一個困擾人們的問題是,為什麼仍不斷有受害人上當?
“其實對於任何一類網路電信詐騙,我們都可以用脆弱性操縱這個概念去理解。”在周由看來,詐騙人員操縱了受害人及其家人的“脆弱性”。以中國留學生家庭為例,周由認為,該類詐騙一個成功的要點就是實行通訊阻斷。此種情況下,孩子遠在中國的父母無法證明孩子沒被綁架,自然不敢冒險。
留學生同樣有脆弱之處。周由記得,自己還在澳洲讀研期間,一位朋友曾問他,借高利貸是否屬於犯罪。朋友接到了自稱是國內警方的電話,對方說,他先前寄的包裹裡有三百多個護照,可能要面臨審判;不過,他們能夠幫忙擺平這件事,前提是得花錢。
周由一聽,便猜到來電的是騙子。可朋友找到他時,已經陸續給對方轉了20萬元,手上沒錢了,這才考慮借貸。周由分析,詐騙人員先借罪名恐嚇受害人,再給他一根絕處逢生的稻草,讓受害人發自內心地相信,他們是來幫忙的,這就對受害人建立了一種心理支配。
回到虛擬綁架的情形中,周由分析,初來乍到的留學生對國外的陌生環境懷有恐懼。另外,他們普遍年齡較輕,缺乏閱歷,更容易陷入假冒公檢法人員以協助脫罪為名索要錢財等騙局中,繼而被支配。
這種支配建立後,受害人會對詐騙人員言聽計從。例如,假借阻止國內警方聯絡受害人之名,詐騙人員會要求受害人關機,受害人會出於對詐騙人員“告知了內幕訊息”的感激而照辦。
不過,縱使是一位瞭解此類手法、閱歷更豐富的人,面對第三代虛擬綁架的精準資訊提取,從容應對也非易事。“突然有一個人打電話跟你講,你有一張法院傳票,並且把你的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證號講出來,你一點都不會慌嗎?”周由說。
對於執法機構來說,對虛擬綁架進行監管與打擊亦有難度。周由發現,此類案件本身報案率就偏低,這使得許多騙子得以逍遙法外。原因之一,是被騙資金能追回的機率極低。
除此之外,便是普遍存在的受害人譴責。受害人大都有一種羞恥感,甚至心理創傷:“被騙是不是我太傻了?”周由在做虛擬綁架的研究期間,就很難找到願意訴說自己受騙經歷的受害人。一位在澳生活近五年、曾就職於悉尼一家華文媒體的華人也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2020年,她所在媒體曾接到當地一名男子的求助,稱其親屬失蹤,希望協助釋出尋人啟事。後來,當地警方證實,他的親屬遭遇虛擬綁架,這個家庭被騙走了20萬美元。她希望深入採訪此案件,但遭到受害人家庭的拒絕。
跨國打擊難題
而在那些已被報告的案例中,警方也很難打擊詐騙人員。周由解釋,虛擬綁架案件裡,詐騙電話的呼叫中心大多位於受害人所處國家之外,收取“贖金”的賬戶則可能在第三國。打擊這種跨國犯罪通常存在執法權與管轄權的問題。莊凱案中,沃倫就提及,聯邦調查局很快發現,詐騙人員在中國,用於收取“贖金”的也是中國的銀行賬戶。裡弗代爾警方相信,中方能將這批詐騙人員繩之以法。
即便不同國家執法機構合作打擊此類犯罪,難題依然存在。廣東警官學院治安系副教授李向玉稱,許多詐騙人員會使用匿名通訊手段,如假電話號碼、網際網路電話或其他數字平臺,這令追蹤他們的身份變得困難。
周由也稱,國家間的正式合作可能要耗費長達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才能完成,詐騙人員很可能利用這段時間銷燬證據、處置資金,並逃避抓捕。
在李春勇看來,遏制虛擬綁架,要堅持源頭治理,尤其嚴厲打擊販賣個人資訊等違法犯罪行為,嚴格保護公民個人資訊。在案件中,如能查實有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利用身份將個人資訊販賣給詐騙人員的,應從重處罰;如有留學中介機構出售學生資訊,且能證明出售行為導致了一定數量的虛擬綁架案,應取締該機構。
除此之外,李春勇認為,一旦留學生家庭遭遇此類案件,國內的受害人親屬還是要及時報警,警方能梳理近期是否有類似案件發生,並判定綁架的真偽,也能透過公安部、使領館等機構瞭解案件發生地的情況。受害人親屬們也需要儘快穩定情緒,及時與人溝通,“因為詐騙人員利用空間距離大打時間差,等時間一過,有可能不是那樣的情況”。
李向玉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按照國內刑事案件辦案程式,警方響應虛擬綁架的報警後,應儘快使用電話追蹤、網路監控等手段,識別、追蹤詐騙人員的位置及身份,電話運營商及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均可協助此類調查。與此同時,警方也要收集通話記錄與金融交易記錄等證據,用於完成案件的調查程式。
李春勇表示,此類案件中,打破資訊屏障十分重要。詐騙人員得手的關鍵在於設立資訊屏障,受害人則要嘗試反其道而行,適時中斷與詐騙人員的通訊,及時向身邊的親朋好友諮詢交流,或者直接聯絡駐外使領館,騙局就很容易被識破。“透過正式渠道交流資訊很重要,不要輕信詐騙人員的話,也不要盲目順從詐騙人員的誘導。國內公檢法機關絕不會在電話裡索要你的身份、銀行賬號這些資訊,不會在電話裡要求轉賬匯款,使領館也不會在電話裡通知當事人在國內有案件需要處理。”
在周由看來,現階段,與其研究如何在末端進行打擊,不如強化在前端的預防,例如反詐宣傳。虛擬綁架既然做到了精準資訊提取,宣傳也可嘗試精準宣傳。“比如說,大學是否可以統計一些有潛在留學意願的學生,我們能否給他們做一些精準的反詐宣傳?講解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出現什麼樣的網路詐騙犯罪,以及虛擬綁架的一些形式。我覺得這種精準宣傳會比廣撒網的宣傳更有效一些。”
(文中周荃為化名)
其他人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