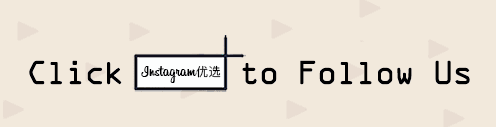沒有一個文青,能逃得過三毛。
我很小便讀過了她的書。
但因年幼,撒哈拉的異域詭事又太濃烈,如刀刻心,如釘印腦,以至於分不出多餘注意力,去關注其他。
直到近日整理書架,重翻了一下三毛,發現不少震驚之處。
有些章節甚至看得瞠目。

譬如《如何面對婚外情》。

在三毛的自述裡,她與荷西堪稱靈魂伴侶。
相遇也好,等待也好,重逢與相戀,避於世外的相守……
都如童話。
再加上,荷西在愛未冷、情未逝之時離世,更使得這段經歷,纏綿如虐文,悱惻如悲歌。

但你一定想不到:
荷西竟然也出了軌。

在出軌前,先得相愛。
否則,背叛不至於成為致命傷害。
他們的愛堪稱傳奇。

初遇在馬德里。
那天是聖誕節。燈火迷離,滿城熱鬧。
西班牙有一個風俗,聖誕夜12點一過,就要向左鄰右舍、樓上樓下一家家地恭賀。
“平安。”
“平安。”
有點像拜年。
三毛當時在朋友家裡過節,零點時,也上上下下地,去道賀,去祝禱。
猝不及防地,遇見一個男孩,從樓下跑下來。
一眼萬年。
三毛在《流星雨》裡,寫過彼時的感受:
“我第一眼看見他時,觸電了一般,心想,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英俊的男孩子?”

彼時,荷西不滿18歲,正在讀高三。
三毛在馬德里大學念大三。
一見鍾情後,高中生荷西瘋批一般追求她。
邀她打棒球。
下雪的日子裡,一起打雪仗。
有時去逛舊貨市場。
沒什麼錢,他們從早上九點,逛到下午四點,只買了一支鳥羽毛。

有一天,三毛正在書院唸書。
有人跑過來:“Echo,樓下有人找你。”
她走到陽臺,一看,就看到荷西。
他手裡抱了幾本書,手中捏著一頂法國帽,緊張得像要捏出水來。
彼時,荷西正少年。年紀太小,不敢進會客室,就固執地站在一棵樹下等。

三毛下了樓,問:“你怎麼來了?”
他不說話。
她緊接著問:“你的課不是還沒有上完嗎?”
他答道:“最後兩節不想上了。”
她又問:“你來做什麼?”
他在口袋裡掏出14塊西幣,輕輕說:“我有14塊錢,正好夠買兩個人的入場券,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好嗎?但是要走路去,因為已經沒有車錢了。”
他們去了最近的電影院。
因為,不需要車錢。

第二天,荷西又逃課來了。
第三天、第四天……
漸漸地,樹下那個高大的少年,成了書院的一個笑話,同學總是喊:“又來囉!”
三毛也困擾。
對荷西說:“以後不要來了,這樣逃課是不行的!”
可是,他照例前來。
風雨無阻,日復一日。
兩個人都沒錢,有時就在街上走,或到皇宮去看看,撿撿皇宮垃圾場的廢物,“你看看這個鐵釘好漂亮!哇!你看看這個……”也覺得甘之如飴。

漸漸地,三毛覺得,這個男孩越來越認真。
可他太年輕了。
他的年紀,根本承載不了“現實之愛”的重量。
彼時,馬德里已入冬,天很冷了。
他們蹲在地下車的出風口,等一點暖氣。兩個赤誠又寒酸的年輕人,凍在板凳上,像乞丐一樣。
她忽然說:“從今天起,你不要來找我了。”
荷西慌了。
他認真承諾:“你再等我6年。我4年念大學,2年服兵役,6年以後我們可以結婚了。”
他不願意放開手,反覆描述兩人的未來。
他說:“我一生的想望,就是有一個很小的公寓,裡面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太太,然後我去賺錢養活你,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夢想。”
他還說:“我在自己的家裡,得不到家庭的溫暖。”
三毛的眼睛,一點一點地霧了。
她想到他們的差異,想到一無所有的現境,無處安放的未來……
還是狠狠心,說:“荷西,你才18歲,我比你大很多,你不要再做這個夢了。
從今天起,不要再來找我,如果你又站在那個樹下的話,我也不會再出來了。
6年的時間實在太長了,我不知道我會去哪裡,我也不會等你6年。
你要聽我的話,不可以來纏我。你來纏的話,我是會怕的。”
他愣了很久。
久到時間,都如同靜止了一般。
忽然,他聲音嘶啞著問:“這陣子來,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三毛說:“你沒有做錯什麼,我跟你講這些話,是因為你實在太好了,我不願意再跟你交往下去。”
接著,她站起來。
他也跟著站起來。
他們一齊走到馬德里皇宮的一個公園裡。
園裡有個小坡。
她站住,轉過臉對他說:“我站在這裡,看你走,這是最後一次看你,你永遠不要再回來了。”
他說:“不,我站這裡看你走。”
她說:“你要聽話,走吧,永遠不可以再回來了。”
為了絕了他的心思,她甚至撒了謊,“從現在開始,我要跟我班上的男同學出去,不能再跟你出去了。”
說完,又擔心傷害到荷西。
無比緊張。
他真的黯然下來。
他低下頭,說:“好吧!我不會再來,你也不要把我當做一個小孩子……我心裡也想過,除非你自己願意,我永遠不再來纏你。”
天已經很晚了。
夜如濃墨,一點一點漫了世界。
他轉過身,走得很快。
後來慢慢跑起來。
“Echo再見!”
他一面跑,一面回頭,眼中明明有淚,臉上卻掛著一抹笑,口中喊著:“Echo再見,Echo再見!”
她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地看他。
馬德里很少下雪。
但那個夜裡,雪落了下來。

他在草坡上跑著,一手揮著法國帽,頻頻回頭,身影漸漸消失在夜色與雪色裡。
她差點喊出來:“荷西!你回來吧!”
可她沒有說。
此後餘生,她無數次想到那一幕,18歲的荷西在空曠的雪地裡,跑著,叫著她的名字:“Echo再見,Echo再見!”

他跑出了她的世界。
後來,果真再也沒去找過她。
很久以後,三毛和同學上街,又遇見了荷西。
他留了鬍子,長大了。幾乎像個大人。
他看見她,走過來,像個禮貌的普通朋友,對她說:“你好!”
她也說:“你好,這是我的男朋友××。”
他跟那人握握手。

然後,說些不鹹不談的話。
再然後,不緊不慢地離開。

不久,她大學畢業,離開西班牙。
回到臺北。
此後一別,就是6年。
她成了中國文化大學德文系、哲學系的教授。
而他,上大學,服兵役,有條不紊地成長和生活。
有一天,來了一位西班牙的朋友。他帶來一封信,和一張照片。
照片裡,荷西穿著泳褲,在海里抓魚,笑得恣意。
她脫口而出:“這是希臘神話裡的海神嘛!”
而信上,荷西鄭重寫著:
“過了這麼多年,也許你已經忘記了西班牙文,忘了馬德里。
可是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在我18歲那個下雪的晚上,你告訴我,你不再見了,你知道那個少年流了一夜的淚,想要自殺……
這麼多年來,你還記得我嗎?
我和你約的期限是6年。”
半年後,她回到西班牙。

6年的時光,改變了太多東西。
當年那個人,還在嗎?
荷西不在。
當時,他在服最後一個月兵役。
她都不太會西班牙文了,用英文寫了一封信,傳到營區去。
信上說:
“荷西!我回來了,我是Echo,我在××地址。”
營裡沒有一個人懂英文,荷西又急又惱,他來信說,不知道她說了些什麼。
但他寄來很多潛水者漫畫,指出其中一個:“這就是我。”
過了幾天,他又打來長途電話:“我23日要回馬德里,你等我噢!”

23日,三毛忘了這事,她和同學去了另一座城,樂不思蜀。
回去後,室友說,“有個男孩打了十幾個電話找你。”
與此同時,一位相熟的朋友打來電話,讓三毛趕緊去她家。
一進門,朋友用手,矇住了她的眼睛,扶著她往前走。
她忐忑不安。
不知發生了什麼。
此時,有人向她走來。
腳步聲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接著,背後伸過來一雙手臂,將她擁抱了起來。
她打了個寒顫。
眼睛張開時,就看到荷西站在眼前。
他穿著一件棗紅色的套頭毛衣,攬著她,興奮地兜圈子。長裙飛了起來。
她尖叫。
她被意想不到的重逢,衝擊得頭腦一片空白。

命運在6年後讓他們再次相見。
是不是意味著,這就是冥冥之中的緣份?
後來,她在荷西的房間裡,看到滿牆照片。
都是她。
發黃的、放大的、紙質的三毛,陪伴了他6年光陰。
她問:“我從來沒有寄照片給你,這些照片是哪裡來的?”
他說:“在徐伯的家裡。你常寄照片來,他們看過了,就擺在紙盒裡,我去玩的時候,就把照片偷來,拿到相館去放大重印,再把原來的照片偷偷放回去。”
“家裡的人看不到嗎?”
“看得到……他們說我發神經病了,那個人已經不見了,還貼著她的照片發痴。”

那一刻,她酸楚不已。
她轉過身,定定地看著荷西:“你是不是還想結婚?”
這次輪到他呆住了。
她說:“你不是說六年嗎?我現在站在你的面前了。”
他依然不敢置信。
三毛突然流下眼淚,她想到分開的6年裡,她經歷的得與失、愛與痛、生與死。
想到她的德國未婚夫因心臟病發,離開人世。
想到她的噩夢與隱痛,遺憾與餘哀……
又說:“還是不要好了……不要了……”
他忙問:“為什麼?怎麼不要?”
她含著淚:“你那時為什麼不要我?如果那時候你堅持要我的話,我還是一個好好的人,今天回來,心已經碎了。”
他說:“碎的心,可以用膠水把它粘起來。”
三毛說:“粘過後,還是有縫的。”
他握著她的手,拉向他的胸口:“這邊還有一顆,是黃金做的,把你那顆拿過來,我們交換一下吧!”


半年後,他們結了婚。

結婚時,親友擔心,他們年齡、經濟、國籍,甚至於學識,都不太匹配。
但三毛想,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品格和心靈。
他們的婚姻持續了6年。

1973年,他們一起,去了撒哈拉沙漠。

1974年,三毛開始寫下《中國飯店》等一系列作品,妙趣橫生地,講述自己的異國婚姻,和沙漠奇聞。
1976年,《撒哈拉的故事》面世。
1977年,三毛出版了《稻草人手記》《哭泣的駝駝》等文集。
1979年,荷西身亡。
年僅30歲。

他們曾經談過死亡。
有一次,一本雜誌邀稿,請三毛寫一篇文章。
主題是:“假如你只有三個月可活,你要怎麼辦?”

她把邀稿信拿給荷西看。
荷西說:“這個題目真奇怪呀!”
當時,三毛正在揉麵,荷西就問:“這個稿子你寫不寫?你到底死前三個月要做什麼,你到底要怎麼寫嘛?”
她繼續揉麵,隨口說:“你先讓我把面揉完嘛!”
“你到底寫不寫啊?”他不知為什麼,固執地問。
她無奈,轉過頭來,看著荷西,摸摸他的頭髮,說:“傻子,我不寫,因為我還要替你做餃子。”
之後,又繼續揉麵。
荷西突然從後面抱住她,一直不肯放開。
她嗔他:“你神經啦!”
他緊摟著不動,她又說:“走開嘛!”
他還是不肯放手,她無奈:“你這個人怎麼這麼討厭……”
話正說了一半,猛一回頭,看到他整個眼睛充滿了淚水。
他突然說:“你不死,你不死,你不死……”
又說:“這個雜誌我們不要理他,因為我們都不死。”
她問:“那我們怎麼樣才死?”
他說:“要到你很老,我也很老,兩個人都走不動也扶不動了,穿上乾乾淨淨的衣服,一齊躺在床上,閉上眼睛說:好吧!一齊去吧!”
可他沒有等到,她也沒有。
荷西在一次潛水時,遭遇事故。
不幸身亡。
再也沒有回來。

我相信,看到此處,你一定滿眼淚水。
為荷西的猝死。
為他們的曠世愛情。
為求不得、意難平與留不住。
可是,我想告訴你,就在1977年,他們結婚的第4年,荷西出了軌。
當時他們從撒哈拉沙漠,搬到了迦納利群島。
有一次,荷西說,他要回西班牙本土,接受19天的“深海潛水”再訓練。
出發前,荷西問:“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她為了省路費,沒去。
那十幾天裡,荷西和她每天聯絡,深情厚愛,一如往常。
可當他回來後,他說,他認識了一個女孩,陷入情網。
又說:“要不是結了婚——”

三毛滋味複雜。
她難受之餘,竟湧上自責。
她什麼也沒說,任由他抱著她,不斷細數那個女孩的點點滴滴。她這時才知道,那個女孩對荷西,也有意。
這種“恨不相逢未嫁時”的錯失感,令荷西和那女孩都無比遺憾。
3個月後,荷西不再提及女孩的名字。
只是依然黯然。
這種沉默令三毛更加痛楚。
她想了很久,內心纏鬥了無數回,終於,她提出了兩個解決方案。
這兩個方案,她都寫在了《親愛的三毛》中,讀來頗為震驚。
第一個方案是:
她回臺北一年。
荷西和女孩一起生活一陣。
如果他們美滿,她就離開,自尋生路。
但如果他們不幸福,荷西只要給她一個電報,她就飛回去,依然做他的妻子。
第二個方案是:
三個人一起親愛相處,一起做親密的朋友、家人和愛侶。
真誠相待,不分彼此。

來自三毛《親愛的三毛》
荷西沒有想到,三毛竟會如此“尊重”他的愛與欲。
他抱著她,流下眼淚。
一年後,一切塵埃已定。
他仍然選擇了她。
她也沒有芥蒂地,回到他身邊。

很久以後。
他們像一對暮年夫妻,坐在陽臺,吹著風,看海上落日。
三毛隨口問了句:“還想她嗎?”
荷西說:“那種愛情,屬於一霎永恆的完成,難忘。至於說我們之間,生活的恩和情扎得太深,天長地久了。”

來自三毛《親愛的三毛》
這段婚外情,至此劃上句號。
他們的婚姻仍在繼續。
如果不是死亡,提前將荷西帶走,她仍然會“憐憫”地、“恩慈”地,和荷西繼續度日。
她的“退讓”與“成全”,超出我們的想象。
她的隱忍,也令人不適。
更令人意外的是,2年後,荷西溺水過世。
那女孩也來了。
三毛和她抱在一起,痛哭失聲。
兩人似乎沒有恨,沒有怨,只有相似的痛苦。
三毛甚至為女孩,介紹了一個原本喜歡自己的中國攝影師。
二人結婚,生了一個孩子,也取了荷西的名字。
孩子叫三毛為“中國媽媽。”

來自三毛《親愛的三毛》
這一系列操作,每一步都炸裂非常。
遠超普通人的理解範疇。
有人問,是不是三毛沒有嫉妒心?事實上,她有。
她說過,她和荷西曾約定不要孩子。
因為,如果生的是個孩子,她會把女孩打死。因為她會吃醋。
如果是個男孩,荷西要把他倒吊在陽臺上。因為三毛會太愛那孩子。
也就是說,他們二人,也有正常人的佔有慾、排他心。可為什麼在面對婚外情時,會如此“奇怪”和“反常識”?
三毛解釋過——
“如果當年我與先生的結合,不是雙方都已在人生裡出生入死地歷練過,我們的處理不可能如此超然和昇華。”
在她看來,婚外情不能因為犯了“錯”,就斷人死。
因為結婚契約,無法保證感情。一個人愛上了兩個人,也是人性的一種可能。
所以,她能“勇敢真誠”地,面對荷西的不忠。
也能“超然”地,接納荷西的回頭。

三毛或許說的是真的。
但這種觀念和操作方式,落到現實裡,堪稱毀人不倦。
而這段關於婚外情的描述,是她用來回復一個讀者來信的。女讀者因丈夫出軌,痛苦得快要死掉了。

來自三毛《親愛的三毛》
三毛將自己的理解和應對,當成一種成功範本,教導給他人。
甚至要妻子,去共情出軌的男人。


來自三毛《親愛的三毛》
但現實是,男性的不忠,跟妻子沒有關係。
跟物件也沒有關係。
紅大爺也有百千伴侶。
你美如楊冪,丈夫也會讀“夜光劇本”。
你賢良退讓如佟麗婭,丈夫也會“夜會兩女”。
要女性去憐憫、去成全、去三人,都是對女性“去人慾”的馴化,和要求女性無限犧牲的聖母化。

來自三毛《親愛的三毛》
她的處理方式,更像是妻妾制度的翻版。
彷彿面對背叛,只有幫著“納”了、隱忍地退居二線,或悲憤地出局……才是解決之道。
但當代女性天高海闊。
多的是可能。
有的是路徑。
實在沒必要複製她的思路。

來自三毛《親愛的三毛》
畢竟,正常人嚮往“曠野”,三毛卻渴望“沙漠”。
正常人尊重自己,而她要愛人類。
參考資料:
1,三毛《流星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6
2,三毛《親愛的三毛》南海出版公司20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