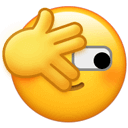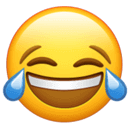我的第一個偶像,是莫文蔚。
記得是在1996年某音樂雜誌一篇介紹香港地下音樂的文章裡,有一禎相片——一個全裸的光頭女人,手裡夾著一支香菸,她塗著菸灰色的眼影,整個人流露出一種孤絕而迷茫的氣息,令人觸目。介紹說,這個女人叫莫文蔚。
當時我正處於所謂的“叛逆期”,看到了這張相片,我感覺找到了知音。於是,我買了她的第一張粵語專輯《全身》,怪得很另類。揹著的大包裡常常扔著幾本書,幾盤磁帶,幾個廢電池和時多時少的錢,亂糟糟地陪著同樣亂糟糟的我在校園裡亂走,帶著耳機聽歌,旁若無人。
在剛剛開始用調變解調器上網的1998年,我已透過網路找到了她的內地民間歌友會併成為僅有的十幾個初創成員之一。我們在聊天室裡興奮地討論她的全新專輯,用龜速網路下載她的數碼寫真,互相加了QQ,並約定將來在北京見面——不過還沒等到我考大學去到北京,我們相互之間已經走散了。
其實走散的遠遠不止這些。上了大學,去了新的城市,過上了從未經歷的集體生活,我小心翼翼融入,不敢一味追求另類,積極加入學生會、拿獎學金、早早為就業做準備。莫文蔚也不怎麼聽了,而是隨大流地跟著室友和同學聽校園民謠、中國搖滾之類,如同每一個正常而激昂的大學生。
年紀更大一些,生活發展出新的面貌,也沖走了舊的印記。人漸漸成熟,懂得世間萬事只能全靠自己,無人可學,無人能救,於是不再需要偶像。正如一首歌詞所唱:一個一個偶像,不外如此;沉迷過的偶像,一個個消失。
然而,前不久在成都看莫文蔚演唱會,當一首首曾經的歌被唱起,我破防了——我又完完整整地想起了從前那個格格不入的少年,是如何從她的歌詞、她的風格、她的宣言中,找到安慰、獲得啟發、得到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
也才意識到,15歲開始聽過無數遍的專輯《全身》《To Be》《I Say》…註定成為了我生命中的某種獨特與勇氣。

如果說我在學生時代有何特立獨行之處,大概是,同齡人都在看《少男少女》《讀者》,而我從中學開始,就一期不落地閱讀《世界時裝之苑》《時尚伊人》以及時不時能買到的港版時尚雜誌。
也因此,那時候,除了莫文蔚,我還有另一個與眾不同的偶像。
2000年伊始,莫文蔚憑藉《陰天》與《忽然之間》,終於全面大紅大紫。同一時刻,全世界的時尚雜誌幾乎每一期都在談論一個人——侯賽因·卡拉揚(Hussein Chalayan)。
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他的最新秀場,滿是期待地猜測他的下一季釋出,熱情洋溢地對所有讀者介紹他,彷彿他是一顆剛剛才被發現的閃亮恆星。
我至今仍記得,第一次在時尚雜誌上看到卡拉揚2000年名為Afterwords秋冬秀場時的震撼:只見幾個模特走到舞臺中間,不緊不慢地拆下單人扶手沙發的沙發罩,魔術一般變成了剪裁利落的連衣裙。更精彩的是,一個模特走到咖啡桌的中間,輕輕一拉,將咖啡桌層層疊疊拉起、再掛在身上——竟是一條絕美半裙!
很多年以後我特意上網找來當年秀場的影片重看,比圖片震撼不知多少。整個秀場迴盪著遊牧民族的無伴奏吟唱,雖然模特展示的是時裝,卻能輕易從中讀懂設計師的鄉愁。
那一季的設計靈感源自卡拉揚與母親的對話。他問母親:如果被迫背井離鄉,你會從家裡帶走什麼?母親答:舊照片,舒服的毯子,還有喜歡的食物。於是,卡拉揚便用高超的剪裁與天才的創意呈現了一次別離。
權威時尚雜誌VOGUE至今仍將卡拉揚2000年的秋冬釋出稱為“史上最精彩的時裝秀(沒有之一)”。而那一年的我,開始將這位1999及2000連續兩年獲得英國年度設計師大獎的奇才視為偶像。



後來,我百折不撓地進入了嚮往已久的時尚行業。後來,隨著時尚雜誌的沒落,我成了獨立的自媒體人;再後來,我徹底投身小說寫作,幾乎與時尚行業完全脫離。
過往20年的職業生涯,令我對時尚祛魅。它再也不是曾經那般,充滿想象力、前瞻度與藝術性的設計行業,而成為純粹的商業——沒有好壞,無謂對錯,只是賣貨。
但,這麼多年,我卻一直保持著對卡拉揚的關注。一則因為,他始終在奮力對抗著商業壓力,我行我素地堅持呈現他獨一無二、天馬行空的時裝設計;二則,在時裝之外,他亦逐漸成為一名頗有建樹的先鋒藝術家,作品十分精彩。
總之,我願視之為偶像的人,總須有令人折服的創造力、剛強不懼的自我、以及對專業的虔誠。
因此,前不久,當被問及是否願意與卡拉揚本人見上一面,我毫不猶豫答應了。正如同買第一排的票去聽摯愛歌手的演唱會,能在有生之年,見一見照耀過自己的偶像,千山萬水,也是值得赴約的。

卡拉揚於2005年在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的影像作品《不在場,在場》
由Tilda Swinton出演
這種藝術形式至今仍被無數同行借鑑、模仿。
見面地點約在雅典,那是卡拉揚鄉愁開始的地方。
卡拉揚出生在塞普勒斯,小時候飽受土耳其與希臘衝突之苦,最終不得不與家人遠走他鄉,童年一度獨自在英國學習生活。1993年,他在倫敦聖馬丁學院的畢業設計便技驚四座。而後,一條“航空郵件裙”更是令人動容——那是他小時候與母親分隔兩地不斷通訊的回憶。
一條由可穿著合成紙裁剪製作的連衣裙,標有詳細的摺疊說明,能夠疊成一個真實的航空信封,透過郵局寄送。你甚至可以在這條“信封裙”上噴灑香水,寫滿內容,寄給對方,再由對方開啟、穿上。
那也是我當年對時裝設計歎為觀止的起點——沒想到世間竟然能有比“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更詩意的鄉愁表達。

到達雅典當晚,我誠惶誠恐地前往卡拉揚推薦的餐廳。沒想到,他已站在門口等我。他鮮少露面,因此我之前只在雜誌裡見過他的照片。這麼多年過去,他已是知天命的放鬆中年,穿著簡單的黑tee黑褲,笑著來迎我。
他選的餐廳,其實是一家路邊攤,專做希臘家庭料理,十分美味。我們坐在路邊,不時有小貓過來討飯,我一邊擼貓,一邊喝酒,漸漸放鬆。
我們自然聊到了2000年秋冬那一場“將傢俱穿在身上帶走”的秀,然後我問他:你的家是什麼樣子的?
卡拉揚說,他自始自終都是一個極簡主義者,他在倫敦僅有一處小小公寓,房子裡除了必要的傢俱,其餘一概全無。
於是我又問:那如果有一天要離開,你會從這個家裡帶走什麼?
回憶,他說。
人生在世,只有回憶,可以帶走,值得帶走。
雖然卡拉揚最著名的設計是關於回憶、關於鄉愁,但實際上,他是這個行業的未來派大師。他彷彿一個從未來回來的人,帶著未來的技術、未來的剪裁,屢屢令當代人大開眼界。
他20年前的概念、設計,放在如今,依然超前,不斷被人借鑑、致敬。這其中,他最著名的“粉絲”,大概是Lady Gaga。
早在2009年,Gaga剛剛火遍全球之時,她最出圈的一個造型,泡泡裝,便是向卡拉揚曾經的設計致敬。

2010年,Gaga在演唱會上穿著一條可以自動張開翅膀的仙女裙,靈感更是來源於卡拉揚前無古人的2007年春夏大秀:111。

在2007年這場秀上,卡拉揚展示了6條完全實現自動化的裙子。他根本是一個瘋狂的工程師,將精密機械巧妙地隱藏在一條條裙子之中,讓裙子實現了自動開合、縮短、收緊、摺疊、變形,從上一個時代的風貌在你眼前當場化為下一個時代的廓形。
實現這一奇觀,不僅是對設計與剪裁的極限挑戰,更是藝術與科學的極致融合,足夠載入時裝史冊。

同一條裙子包括帽子會自動從左依次變到右
2011年,Gaga終於與卡拉揚正式合作,後者幫她設計了聲名大噪的“繭”。在當年格萊美上,Gaga就躺在裡面,被舞者抬著走過紅毯。而後,她在舞臺上破繭而出,高唱《Born This Way》,一戰封神。


我問卡拉揚:被公認領先時代20年,你覺得這是幸運、還是詛咒?
這個問題令卡拉揚沉思了片刻,半晌,他才緩緩回答我:我覺得是詛咒。因為有些未來,不敢去想。或者說,很多東西,都沒有未來了。
我完全懂他說這句話的意思。在這個時代,堅持某些觀念、某些原則、某些理想,簡直會被當作笑話。下沉與叫賣,才是時代最強音。
卡拉揚顯然為他的清高與堅持付出了代價。如同每一個藝術家,在屢屢面對商業倒逼之時,他總是選擇出走。如今的他,在藝術創作之外,選擇在柏林一所大學任教,他說自己特別喜歡面對年輕的學生。
“如果改變不了現在,那麼就努力去塑造好一點的未來。”

2000年春夏“飛機裙”,史上第一件可遙控開合的時裝。
在雅典的第二天,卡拉揚帶我去了希臘當代藝術博物館,站在一覽雅典全城的天台上,他笑著問我:你真的喜歡時裝嗎?
我說,沒那麼喜歡了。其實在你的所有作品之中,最最打動我的是2015年在倫敦沙德勒之井劇院公演的現代舞劇Gravity Fatigue。
卡拉揚擔任創意總監,他把人與人之間變化莫測的關係具象成了舞蹈演員身上的戲服。男人和女人在其中糾纏、角力、試圖控制或掙脫,卻無人如願。毫不誇張地說,我之前在網上看過其中幾幕,感同身受地流淚了。那些文字難以言說的隱情與痛感,被音樂、服裝、舞蹈準確表述。
“哈!那你的內心一定有一個破碎的小孩”,卡拉揚一針見血地說。
“你的內心不也有嗎?”我喜歡他,便是我從他的作品裡,感受到了我自己。
美感之外,能傳遞情緒、與人共鳴,才是好的藝術,好的設計。
“已經被愛治癒了!”,卡拉揚說這句話時,笑得像個孩子。


是的,在雅典那幾天,我對卡拉揚並無太多問題。只是近距離地觀察他,聽他講,讓他與我想象中的那位偶像合二為一。
被愛治癒的卡拉揚,和審美一致、志同道合的靈魂伴侶共同生活多年。所有生活的難,因為被愛、被懂得、被支撐,而不足掛齒。他可以任性地專注於更先鋒的藝術創作,審慎地選擇合作伙伴,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將自己的設計有選擇地流傳。
如今若想穿上卡拉揚親手設計的時裝,最好的途徑,是透過Fabrique,一個極為真誠的設計師集合品牌。
某種程度上,Fabrique所做的事,也是在這個時代逆行——當絕大多數品牌都不再強調設計師,每一季只是不斷複製、堆砌熱賣元素之時,Fabrique卻攜手全球300多位優秀設計師,持續不斷合作推出獨家作品,並以可負擔的平易售價,令大多數人都可真正擁有高品質的大師設計。

Fabrique格外尊重設計。
在下沉的時代,品牌被紛紛裹挾走進了直播間、並把資源全部砸給了所謂的流量,Fabrique仍在花大力氣推廣設計師,讓消費者真正瞭解設計,而非被誰粗暴帶貨。
事實上,我能面對面地見到卡拉揚,便是得益於SEE YOU IN Fabrique的大力支援。這個純文化的專案,代表了Fabrique對設計的虔誠。它安排消費者和愛好者,與合作的設計師直接見面,自由交流、充分相處,建立起一種最有價值的連結。
有一些事,無關消費,只為熱愛。

我與卡拉揚在雅典
像卡拉揚這樣孤標傲世的設計師,願意與Fabrique合作推出大師系列,也是感念於品牌這一份“相信設計力量”的真誠。
除了那些引領先鋒概念的極致設計,卡拉揚的常規女裝,是持之以恆的簡潔、現代與理性。他設計的大衣、外套、襯衫與裙裝,可以完美構建任何一個當代獨立女性的日常衣櫥。
所以,在Fabrique,你能以意想不到的親和價格買到卡拉揚直肩立體剪裁大衣。在經典廓形大衣的肩部上呈現雙層立體結構,口袋與腰部合二為一的結構線設計剪裁,這些都是卡拉揚的標誌性設計手法。


還有那些剪裁利落、凸顯幹練的都市風衣,都是卡拉揚最早作出的設計。
1993年入行的他,早已在為2024年的你,打造職場專業形象。

其實Fabrique的大師系列,除了卡拉揚,還有多位頂尖設計師參與。譬如Raf Simons的愛徒Damir Doma,完美繼承了當代義大利極簡主義的衣缽。他的設計,便是傳說中“看起來毫不費力”的輕鬆但高階。
而與Fabrique聯合推出的限量作品,更是大量以亞麻,桑蠶絲等天然面料,去支撐他的極簡設計和精妙剪裁。
絕對是最有價效比的高階成衣。

我時常對身邊年輕的女孩子推薦Fabrique,因為這就是可負擔的高品質。
不只因為它的每一件單品均來自有名有姓的設計師之手,還在於以大師系列的輕鬆定價,你卻能買到極好的皮革、針織與毛呢。


想起20年前,我剛入職場的時候,設計師也好,高品質也好,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以我當年的收入,光是想要穿得體面,已是煞費苦心。
如果說,這20年間,世界有什麼樣的積極進步,那或許就是像卡拉揚這樣的設計師,以及如Fabrique這樣的品牌,在積極推動設計的平民化。他們主動打破商業的藩籬,讓設計成為每個人不但看得懂、且消費得起的生活日常。
而我也能在20年後的今天,向你驕傲地介紹我昔日的偶像,不是以頂禮膜拜的方式,而是如同舊友一般介紹給你,你可以真正地接近他,透過他的設計瞭解他,然後也許也會和我一樣,喜歡他。

最後,想說一點別的。關於偶像,關於成長,關於我們自己。
我們的朋友,尤其是我們愛過的人,當他們走進我們生活之時,帶來了他們的喜惡、他們的觀念、他們的品味,而當他們離開之後,這些東西卻留了下來,有些成了回憶的憑證,有些固化成了我們自身的一部分。
可是,人這一輩子,萬萬不可丟棄的,卻是那些我們原原本本就喜歡的東西。它們是我們最本能的選擇,未受影響的判斷,曾經給了我們獨處時的快樂,代表了原原本本的我們。
所以,要一直聽自己喜歡的歌,看自己想看的書,穿自在的衣服,不要因為急於融入與討好而人云亦云,不要因為任何人去接受我們本能排斥的東西。
的確,偽裝有時候是社交和建立關係的必須。但到最後,卻是真正屬於我們的喜惡、觀念與品味,才能成就我們的獨立、堅強與自由。
親愛的我們,勿忘我。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