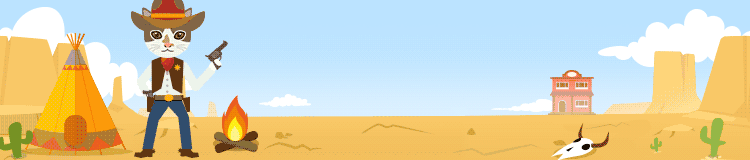本文是圓方的第1162篇原創
(點選標題下方小耳機標誌可收聽音訊)
01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裡記載了春秋時期齊國名相晏子出使楚國時的一則小故事:
晏子將使楚……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
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
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
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這就是著名的“南橘北枳”的成語故事,比喻同一物種因環境條件不同而發生變異。
02
這個五一假期輿論最關注的熱點,是一樁由感情問題引發的,醫療學術培養標準大討論。
這個“學術培養”標準就是北京協和醫學院推行的“4+4”醫學博士培養模式。
這一制度據說是效仿美國醫學教育體系,允許非醫學背景的本科生透過4年醫學博士課拿到文憑,其核心目標是:
希望能夠藉此打破學科壁壘:透過吸納理工、人文等多元背景人才,推動AI醫療、生物材料等前沿領域發展,從而“跨界培養複合型醫學領袖”。
與傳統醫學生需經歷5+3+3年的漫長路徑相比,“4+4”學生僅需8年即可完成從非醫學專業到醫學博士的跨越。
然而,協和首屆“4+4”畢業生董某瑩的個案來看(從哥倫比亞大學二級學院經濟學本科跨界成為胸外科規培醫生,之後僅用1年完成3年規培),這個制度的好處是一點沒有體現,而制度設計中的漏洞卻暴露無遺。
而當“董小姐”這樣的當“跨界精英”以碾壓式速度超越傳統醫學生的職業路徑時,這場爭議已從醫學教育改革演變為社會公平的集體焦慮。
03
而在所有的質疑聲中,來自醫生群體的質疑是最多的。
因為中國醫生群體,是高度依賴學歷認證的生態,以及存在高度的“學術鄙視鏈”的。在醫生群體中,“4+4”制度引發的震盪,遠超其他領域的影響。
醫生群體之所以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包括與之配套的高收入。其實跟這個層層累加的學歷門檻是分不開的。
傳統醫學生一般需經歷12年以上系統訓練才能畢業,這是時間成本。
畢業完成之後還要經規培幾年的訓練,來完成病例積累,這是經驗成本。
不用說這後面還有一系列的科研,論文,專著。主治,副主任,主任等排序,等等等等。
可以說,中國現行的醫生體系,就是在這層層巢狀的學術認證下面所形成的。
而這個“4+4”制度的三重衝擊直接動搖了這一根基。因為董小姐這樣“開玩笑式”的選拔體制,直接摧毀了醫生所共同遵循的職業護城河。
其實不光中國醫生群體很難接受這樣的事情。比如在韓國,去年引發醫生大遊行,導致政權不穩的一個事件關鍵,就是韓國政府擬放寬更多的醫學生入學的名額。
01
那4+4這個制度本身真的有問題嗎?其實也未必。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4+4在中國,之所以變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實某種程度上的確是“土壤”問題。
美國的醫療體系以私立醫療為主,中國的醫療體系以公立醫療為主。
美國的醫學生畢業,其實才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後面其個人在醫院裡面能否發展還是要靠真刀實槍的醫療水平。換句話說,美國的醫生某種程度上是更市場化的。
學歷更多的是一個准入門檻,而不是競爭力所在。在中國,醫生學歷,某種程度上跟行政崗位,甚至編制是掛鉤的。以先以醫生的名義解決編制,後面再往行政崗位上去走,也不失為是一條快車道。
董小姐事件中,導師權力、科室人脈等非制度因素,讓規則成為橡皮圖章。換句話說董小姐,可能並不是衝著要去做一個好醫生而努力奮鬥的。當下這個醫生的崗位可能只是他未來職業生涯的一個跳板。
這正如枳樹雖形似橘樹,但其果實酸澀的本質源於淮北水土中的權力鹽分。
05
是否應該全盤否定4+4這樣的制度呢?其實一刀切也不對。
在這個以AI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到來的時代。我們的確需要篩選出來更多的天才投身於醫療事業當中。
比如說如果這一次的當事人是一個高中參加全國奧賽拿到冠軍,本科在北大學數學和AI,然後博士跨界到4+4。然後立志要做AI和醫學的融合的這樣的學生,想必大家可能意見就不會這麼大了。
那應當如何處理?其實也很簡單。
“透明”兩個字即可。
招生流程全透明公開
公開推薦信內容、面試評分細則、本科專業成績等原始資料,引入第三方審計。同時把個人的家庭資料,檔案全部公示,包括所在本科期間取得的成果。
畢業答辯全透明公開
所有4+4的學生,必須讓自己的博士畢業論文經得起全社會的檢驗。同時應該具備比大部分博士畢業生更高的水平。才能夠畢業。
在這樣“嚴進嚴出”的方式。如果還有學生敢於選擇這條路,同時願意接受社會監督,又甘願承受可能畢不了業的風險。
我們為什麼不為可能存在的天才式人物,留一條更快的成長路徑呢?
“4+4”制度的爭議本質是一場關於醫療資源分配權的博弈。
當協和試點班45個名額成為階層躍遷的“特快列車”時,我們更需要思考:
如何讓醫學教育既保持對多元人才的開放性,又不淪為特權遊戲的遮羞布?
答案或許藏於晏子的古老智慧——唯有讓制度設計的“水土”足夠清澈透明,才能既留住橘樹的甘美,又杜絕枳樹的酸澀。